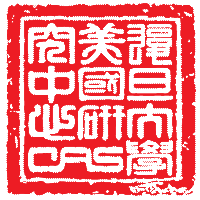2020年8月罗艳琦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得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与导师吴心伯合影
《西游记》中,孙悟空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学得一身本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不啻为我的“斜月三星洞”。毕业多年后,仍不时想起阳光透过中心的玻璃屋顶在大厅地板上投下的明亮的光斑,104号报告厅门口的白色桌椅上坐着的零零散散的学生,中心图书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美国外交档案》(FRUS),每到圣诞节前大厅里准时亮起的高大热闹的圣诞树……在美国研究中心度过的5年博士时光,为学生阶段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成为日后工作、生活无尽的知识和力量源泉。那时候,每天最大的“痛苦”无非是图书馆心仪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读了几篇文献没有收获,论文进展不佳,这些“日抛”痛苦被时间的滤镜镀上学生时代特有的青春光晕之后,也显得珍贵可爱。

美国研究中心大厅
大学要学什么?
《礼记·大学》开篇的一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现代同样有思考价值: 大学究竟应该学什么?物有本末轻重,事有源流始终,大学不仅是认识世界复杂性、多样性的窗口,还应是掌握解析工具、习得处理方案的场所。美国研究中心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结构观、方法论。
对结构的关注。刚入学不久和导师吴心伯老师谈读书心得体会。吴老师听了我的报告后说,到了博士研究生阶段,读书不能只关注史料、案例、信息本身,而要看结构,要看作者怎么谋篇布局,怎么叙述一组复杂的关系和进程,怎么论证自己的观点。自此之后,我开始有意训练自己“看结构”的能力,论文读完一遍后,在笔记本上单独把框架写出来,逐渐开始对行文结构、谋篇布局方式有了概念;慢慢也能看出论述技巧,比如增加某一部分案例可以使论证更充分。从微观来看,“结构”是关于如何组织一篇文章;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结构是关于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是对本末、先后的区分,是对自身精力和资源的分配。
对方法的关注。大家常说“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其实“渔”说的就是要掌握方法。在美国研究中心学习期间,收益最大的就是做研究的方法。吴老师常说,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翔实准确的历史材料,科学规范的理论框架,是好的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历史学习“不怕旧”,研究方法“不怕新”。上海天气潮湿,美国研究中心图书馆里有些老旧的英文原版书籍纸张已发黄,有些书页边都有了霉点,仍然是同学们借阅的“常客”;新发现的网络数据库、新的数据分析软件也是老师同学们经常讨论交流的内容。
博士学位论文是如何炼成的
博士学位论文几乎是所有人在学生阶段最大的研究项目,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其实就像管理一个历时多年的项目。文科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像理工科是实验室团队作业,主要涉及人就是自己和导师。大到如何选题、破题、布局,小到如何搜集权威资料、如何分配一天的工作,既是对个人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体力、精力的考验,也是对师生配合度、默契度的考察。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阶段是非常痛苦的,与吴老师反复沟通、修改,确定研究的内容、时空边界、资料来源、进度安排。有次讨论时,吴老师在一份文稿背面手写了整页纸的框架设想,这份“草稿纸”我至今还保留着。真正开始写作后反而显得“风平浪静”。吴老师对学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安排是标准的工程化推进,要求我们写完一章,马上交给他审读,然后边写下一章、边修改前一章,如此滚动式推进。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导师和学生而言都是节省时间且精准高效的。听闻有的导师在开题后便鲜有过问,要求学生初稿全部完成后再一并修改,但博士学位论文体量太大,颠覆结构、满篇重写的“灾难”时有发生。
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生活就是每日在寝室、图书馆、食堂之间三点一线往返,几乎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查资料、读文献、写论文。当时满心想着尽快毕业,早日结束这机械重复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简单纯粹、能够长久专注于一件事的时光是学生时代才能有的奢侈。
“吴心伯老师的学生”
“复旦博士”“吴心伯老师的学生”无疑是光环,但更是压力,是鞭策、督促我们不断成长进步的动力。记得入学之初,学院的老师就说“做吴心伯老师的学生是很幸福的”,那时候哪里知道这个“幸福”意味着什么。

2019年8月,在第七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作发言交流
吴老师治学严谨,对自身和学生都是严格要求。刚入学时,学长传授“师门规矩”: 所有美国研究方向的课程必须选修,每次上课,一定要坐前排;只要没有上课,有相关领域的讲座一定要来听,听讲座一定要积极提问。果不其然,如果某节课我躲在后排,一定会被吴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毫不留情地拎到前面去;如果偷懒不去听讲座,就会喜提吴老师亲自电话问询“为什么不来听讲座?”如果听讲座不提前做功课,或是一不留心走神,吴老师在提问环节忽然点我发言时必定面红语塞,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为了不当众出丑、舌头打结,久而久之,吴老师的严格要求也练就了我们扎实的学术功底、敏捷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在博士二年级时,有次吴老师召集他所有在校的博士生去他办公室,让我们传阅一位8年未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学长的“肄业书”,那种“惊恐”、震撼的感觉记忆犹新。现在想想,这也是老师对我们的“底线思维”教育。
除了严谨治学,吴老师特别要求知行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深入调查研究、获取一手资料,这不仅是吴老师一贯的要求,也早已成为美国研究中心踏实学风的底色。吴老师积极推荐我们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名师来复旦讲学,鼓励资助学生出国开会、研学,不仅是获取知识、学习外语的机会,也是与别国的同辈群体认识交流的重要途径,在对外交往中拓展了我们的世界观,认识到世界和人生有如此多的可能。

2017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交流学习

2016年8月,参加中韩青年领导力项目
“放牛班的春天”
我们博士班的微信群名叫“放牛班的春天”,博士二、三年级期间,我们班里一大半人在美国做访问交流,还有一两人在欧洲,竟真成了“放牛班”。当时3个女生在美国东海岸从北到南依次排开: 刘青尧博士在纽约大学,李红梅博士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我在最南边的弗吉尼亚大学。我和红梅离得最近,从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Charlottesville”,中国人称其为夏村)驱车去华盛顿特区单程2个多小时,我经常借听讲座、参加会议之机,在红梅处小住几天。犹记得那年华盛顿特区樱花盛开之际携手同游,我们一路从国会山走到波托马克河边林肯纪念堂,坐在方尖碑前的草地上谈天说地,很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畅快惬意。美国没有国内发达的高铁网络,纽约就显得较远了。寒假期间我们去纽约看望青尧,受到这位成都人粉蒸肉、麻辣香锅、卤鸡脚的最高礼遇。
2018年6月,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第八届美中和平论坛
我们在美期间,正值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这位“素人总统”野心勃勃地提出一系列新政策,仿佛是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着从上至下的大辩论。我们发现,哥伦比亚特区的政治氛围最为保守,要求对华脱钩、封锁制裁之声不绝于耳;纽约和波士顿地区次之;世外桃源一般的夏村则更学理。当时我的美方导师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组织大家研读了好几节课“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对日本的油气禁运,以学者的方式隐晦地表达着自己对时局的立场。现在回看,那时正值大变局前夜,风云千樯,身在其中的我们哪里知道,或许当时挤在后排旁听的一场讲座、辩论,影响了未来的两国关系甚至历史的走向。

2017年在美访学期间,参观纽约“无畏号”航母博物馆
除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官方校训,复旦大学一直有句流传甚广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坚守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敢坐、甘坐冷板凳研究无用之用,复旦人谈起“自由而无用”都是自豪骄傲的,自由而无用其实是热烈而勇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研究中心是我国对美研究的重镇,它本身就是开放包容、沟通互鉴的标识。我毕业离校前,吴老师送给我一套美国研究中心出版的丛书,大致是希望我不忘初心、继续美国研究的意思。事实上,美国研究中心严谨、务实、自由、包容的学风早已给一代代学子留下独特的印记。这里的求学经历、学到的知识技能、同窗的师生好友,都成为最宝贵的财富,伴随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探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