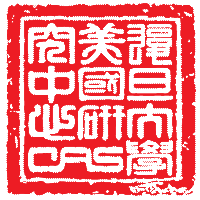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简称“美研中心”)迎来了不惑之年,导师吴心伯教授给我布置了一份“作业”,尝试写一篇美研中心读博记,与有荣焉,欣然领题。
首次进入美研中心读书,是硕士时期,很多硕士专业课是美研中心老师开设的,上课地点就在美研中心二楼教室,我们便获得一般复旦学生没有的机会,进入美研中心。那时美研中心只建成了靠近邯郸路这边的三分之一,靠近国权路、靠近经济学院这两边都还没有建,经济学院大楼也还没有建,这使得美研究中心“离群索居”,而且门卫严格,复旦学生一般进不去,再加上在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研究以及中美民间外交中的地位高,给人一种很高远的感觉。
美研中心,一楼是学术会议室,二楼是教室,三楼是图书馆,四楼是教授们的研究室。在一楼的会议室,作为学生,跟着老师们见过很多美国政要和全球学界精英,包括2000年时,与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来的拜登总统面对面交流,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在二楼教室,我们经常去上课,二楼走廊的小圆桌经常成为自习桌。三楼的美研中心图书馆,那时优先保障美研中心研究人员利用,即使是国政系的学生也不让进。图书馆值守的张阿姨,摆一张大桌子对着图书馆门,嗓门洪亮,把关很严,进去要靠“混”,“混”多了,张阿姨虽嗓门大但本心仁慈豪爽,不仅放你进去,还特别安排让你取了刊物书籍到靠近最里面的一间小小阅览室去看着。美研中心图书馆里面国际关系及相关学术期刊门类齐全,包括当时很负盛名后面遗憾停刊的《战略与管理》,一排排书架满满当当,都触手可及又非常集中,这比“浩瀚”而大众的文科图书馆好多了,书架旁边宽敞的阅读空间里摆放着宽大舒适的几张皮沙发和一台复印机,阅读之余可以坐进舒适的沙发里躺一会儿,再后来靠邯郸路一侧又摆放过一排靠窗的书桌,冬春来时,阳光一早跑上书桌,陪着你看书,温馨清静。四楼,都是教授们的办公室,那时候走廊铺着红地毯,走廊两侧和头顶都是白得亮眼的粉墙,教授们都关着门潜心学问,走廊静悄悄的,想着老师们的严谨,走在里面很紧张。

2012年访问华盛顿
硕士就读的时候,曾经常在《复旦青年》《南区人报》撰写一些国际政经时事的分析,后来又有机会被聘任为《南区人报》(后改名《复旦研究生报》)执行主编,有一次采访了美研中心主研核不扩散与军备控制的沈丁立老师,看到我在校园报刊写的一些文章后,沈老师邀请我在《解放日报》一起写《书生天下》栏目,就国际政经事件发表一些评论和分析,当时受到邀请的学生一共两名,我觉得十分荣幸。由于这些积累,毕业时,同宿舍学弟的老乡,给了我《21世纪经济报道》驻上海一位编委的新浪邮箱,那时《21世纪经济报道》刚成立3年不到,我便给这位编委写了封求职自荐信并附上简历,编委刘老师就让前台安排我去面试,后来刘编委当了主编。当然,我同时也给《解放日报》写了一封求职信,《解放日报》打理邮箱的老师非常好心地告诉我,看简历挺合适,不过按照流程,你要走学校老师、院系这样一路的推荐流程才可以进入《解放日报》的流程,加上硕士时论文方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并十分信仰经济学简洁有力的分析逻辑,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21世纪经济报道》,从政经记者干起,先是走遍田野,到后来担任国际部总监和头版委员会副主任,走访了欧美、亚太和周边一些大国。
那时候,《21世纪经济报道》如日中天,在美国、英国、非洲、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都派有记者,在纽约和华盛顿被描述为“the combination of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New York Times”,我也有机会接触和采访全球商贾政要、知名政府智囊及学者,包括一些500强企业领袖,一些国家的总统、总理、部长们,也有不少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省市的领导人,那时候还是地方领导和政府智囊,向他们提出问题并寻求得到他们的分析和看法,学者当中就有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吴心伯教授。
因为硕士期间在美研中心上过吴老师的课,课程论文得了“优”,吴老师史学科班出身,功底深厚,研究美国战略、外交与中美关系,注重理论和实务,尤其注重策论解决问题,中美经贸投资又很活跃,贸易摩擦、汇率摩擦也不断,便经常找吴老师采访请教,而吴老师各种工作安排得很满,说了采访30分钟,不会到31分钟,但对我的采访总是慷慨支持,有时觉得我没有领略到位的地方,就亲自敲键盘帮我修改,从内容表达准确到标点断句得当,这让我的报社同事有些羡慕。实际上,这既是吴老师对学生的教导,又是对自己言行的严谨要求。
在美研中心四楼办公室采访之余,有一次吴老师邀我喝茶,同我说文解字“安家立业”四字,关心我早日成家立业,他说,“安”字字形意思就是男子家中(宝盖头)里娶了女子才能安心做事,“家”字,在农耕社会,家中(宝盖头)养猪(豕)就是有业,有业才有家。我从农村来,有过家中养猪卖猪换日常生活开支的经历。吴老师这样一解说,顿时觉得这个道理好强大、好深刻。后来,我举办婚礼时,吴老师是证婚人,非常荣幸,这也是吴老师第一次担任学生的证婚人。
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国际新闻主要关注跨境投资、人民币国际化和经济外交三大关键词。而中国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次贷危机前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到30%左右,美国下行到25%左右了,随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一场国际关系话语下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已经在悄悄进行,当时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接受我们采访时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全球龙头企业的时候,世界权力(力量)就开始向中国转移,这让学国际政治的我机警起来。后来博士学位论文中计算了: 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总量在2015年赶超美国,按照名义价格,2035年赶超美国。按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IPE的分析逻辑来推演,这种经济关系变化必将影响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而外交反过来又塑造国家间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变化和关系重塑就要发生。由于中美两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过半,中美(经济)关系是全球包括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制定发展战略和进行业务布局时必须考量的基本变量。这一点放在当下的情景中,已经十分显著。2015年后,中美经贸摩擦日益激烈,当前中美经济外交牵动几乎每家企业的供应链、产业链和市场布局。而中美(经济)外交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塑造力量,研究好中美经济外交的背景、特征、变化逻辑,就能把握好趋势。

当然,系统思考还是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前的思考还是朦胧的、零碎的。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博士学位的攻读。在吴老师的指导下,论文聚焦中美经济外交。
我正好是吴老师指导的第十位博士研究生,可能是考虑到我已经工作6年了,会有所疏松,吴老师安排了一次特别谈话。谈话重点是,每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是一章一章地过,你也没有例外,大龄青年的我瞬间就感觉到血压上升。一章一章过,就如考驾照时教练坐在学员的旁边,随时给你纠正方向,甚至拉下制动紧急刹车,直到你领取了驾照,可以驰骋世界。有段时间,论文进度有点慢,没有及时提交新进展,某天在文科楼六楼进电梯时遇到了吴老师,一只腿已经迈进了电梯,这时被在10米开外走廊拐角里刚出来的吴老师看见了,吴老师不失时机地大声地宣布:“罗小军,你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电梯就关上门,从六楼下到一楼了。论文写作,吴老师要求严格,也督促得紧。还有一次,正好国庆长假,带着夫人和孩子回老家了,吴老师一个电话打过来,问道: 你在哪里?论文进度如何?只好弱弱地说回老家了。后来见面,吴老师宽厚地说,论文要写好必须有整块连续的时间投入,有整块连续的时间投入才能进行深度思考。吴老师是位严格而宽厚的长辈。
无论是读吴老师的书、文章还是听课或者采访、演讲,吴老师逻辑的严密性,观察和分析的层次性、立体性,总能带来主流、敏锐而精准的前瞻判断并提出具体对策,这也深深影响了我的(论文、商务)写作,我把吴老师的本领之一领悟为充分掌握材料、事实和严谨的逻辑分析,材料充分、逻辑扎实,观点就自然靠谱了,终于在某天凌晨写得虚脱时,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把中美经济外交和中美经济关系清晰分为: 初始化阶段、正常化阶段、机制化阶段、包容化阶段和竞治化阶段五个阶段(论文研究中美经济外交时间段截至2012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家关系常态有合作、竞争和冲突三种基本形态。竞治化,治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上是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竞就是中美关系进入了竞争阶段。当然,吴老师总觉得不是太满意,直说平平,自觉也是下的功夫还不够到位,尤其是材料掌握很有局限,直到论文预答辩时,专门研究中美经贸关系包括汇率问题的潘锐老师给论文中美汇率博弈内容当场点了赞,评价为翔实清晰,吴老师整个人才有点轻松起来,并说,看来论文还是有点可取之处,露出了博士学位攻读期间见面难得的笑容。后来论文送审,三个优秀、两个良好。
带我这个博士学生,让吴老师紧张了6年(2008—2014),用后来吴老师的话说是,我当时以为你出不去了(毕不了业),你后来还是出去了。毕业后,趁热打铁赶紧把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出版了,这就是《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1978—2015中美经济外交》,书的封面上写道:“不必忌言责任,更无须忌讳竞争。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而中美关系决定了世界未来。”正好2016年4月书从出版社寄到的时候,是我公司举办第三届全球并购峰会,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应约到峰会发表主题演讲,而他也就成为我这本书第一个赠书对象和读者,送书给他,他非常高兴,桑切斯是中美民间经济外交的活跃人士。当时自觉功力尚浅,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还大有可改之处,又怀着美好愿望,当时与出版社谈版权的时候,把出版社的版权从10年压缩到5年,计划着以后每5年更新出版一次。现在过去了10年,没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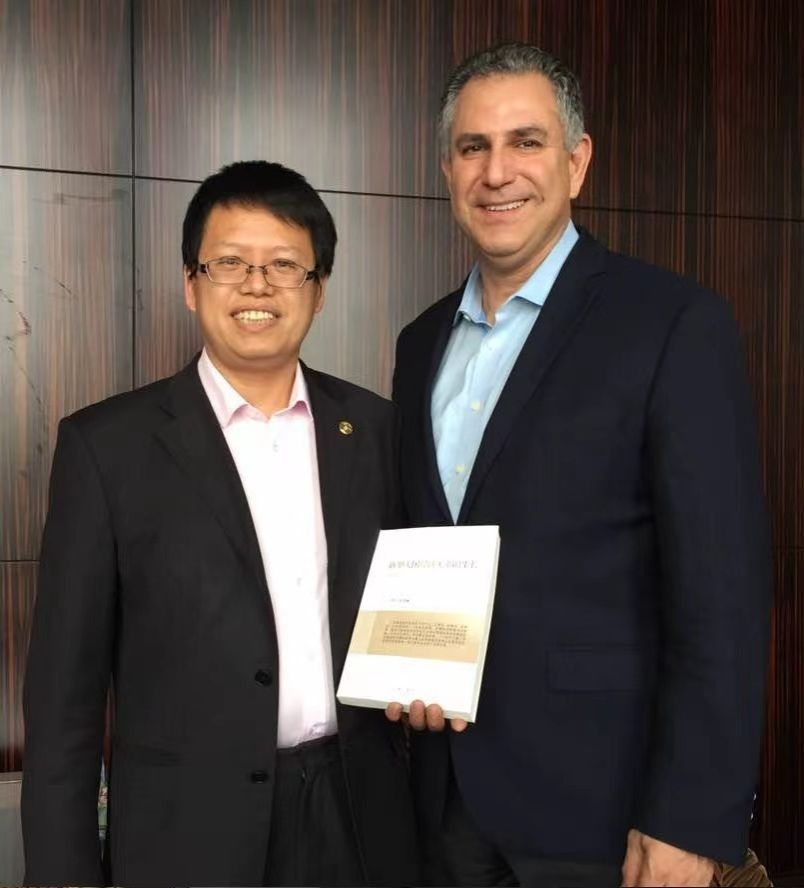
赠书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
2014年,我从美研中心博士毕业,到现在离开了美研中心11年,毕业后先后创办了跨境并购平台公司晨哨集团、并购精品投行普利康途。实际上,我一直不曾离开,创业后也一直得到美研中心老师们、师兄弟姐妹们的支持和帮助,恍如一直在美研中心从事“读博士后”的工作的感觉。
现在,美研中心成立四十周年了,四十不惑,正是青年更有作为的时刻,放在当下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背景下,也是如此,国家和社会都对此有更多的需要,祝福美研中心越来越好。而我从踏入美研中心教室上课开始至今也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事业,一路得到老师们的指导、关心和支持。
2024年,吴老师因其“让学生学有所得、处事有方、成长有道”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成果而被评为复旦大学钟扬式好老师。一位同门师妹总结得更好,她说,吴老师是严父式导师。严师如父,长情滋养,这样的描述再恰当不过,师门兄弟姐妹高度认可和感恩。
学生对大学的情感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师的关怀,犹如孩子对于父母的爱一样。饮水思源,我们该如何有点回报呢?从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开始吧。如吴老师所教导,做学术研究,既要有象牙塔里的成功,也要有社会意义上的成功,对社会有贡献。那么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教育,便是既要取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就,也要发挥自己求学所长,服务于企业、社会和母校。力有不逮,但用此心。
作者系普利康途管理合伙人,晨哨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8级博士研究生 罗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