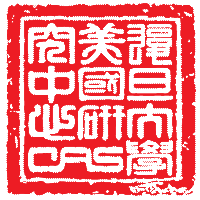在我平凡人生中,最幸运、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入名校、拜学名师。二十年前,我考入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在吴心伯教授名下攻读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这不仅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三年复旦探赜学海的喜悦与艰辛,至今仍历历在目、铭刻于心。今年恰逢复旦美国研究中心迎来四十华诞,借此重拾那三年之宝贵时光,追昔抚今,并向所有指导、帮助过我的复旦师长和学友致以敬意和谢忱!
我想用三个词来形容本人在美国研究中心的求学历程: 仰视、沉浸、回望。
一、 高山仰止,梦想成真
复旦大学的校名取自《尚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底蕴深厚、地位崇高,办学成就蜚声海内外。在我心目中,“复旦”就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山,只能仰望兴叹、难以企及。但最终,我非常幸运地成为复旦学子,至今思来仍似梦幻一般。激发我名校梦想的是对学术的向往与冲动,稍许也有“天道酬勤”的自我慰藉;而助我实现梦想的是吴心伯老师的知遇之恩,以及众多师长的指导与鼓励。
2001年,我考上云南一所省属高校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对于一路靠自学而走出农村、迈入高等学府的人来说,也算是一件很不易的事情。当时该校盛行考博之风,记得入学之初,学院将考上博士生的学长名字张贴在公告栏上,其中不乏考上北大、复旦等名校的学长。我钦羡不已,也深受激励。在入学后不久,美国“9·11”事件爆发,当时有位师兄从“美国之音”第一时间获悉此事,在宿舍大谈阔论,我听后非常好奇,后来查阅相关资料,逐渐对国际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便决定报考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备考过程中,我了解到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在国内首屈一指,而吴心伯老师是当时复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被称为国政学界“中生代”的代表人物,有“民间外交家”之誉。我不知道哪来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勇气,竟然报考吴老师的博士生。到后来我才知晓,吴老师招收学生并不以出身门第为标准,而是唯才是举,而我所谓的“才”则是持续的坚持和韧劲。我的考博过程并不顺利: 第一次考试未进入面试;第二次虽然进入了面试,但怎奈发挥不佳而名落孙山;当我第三次以较高成绩进入面试时,记得吴老师的第一句话是“陈宗权真是锲而不舍啊”,我听后,激动、感动之情涌上心间,这是对我考博过程最好的鼓励,而这句话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2006年5月参加第五届全国高校政治科学类研究生学术研讨会
我考入复旦的那一年,恰是美国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当时国内多所高校的国际政治学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则已经是大师名家云集、学术新星璀璨的国际关系学研究重镇和智库高地。引领我进入这座高地的是倪世雄老师的著作《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当年我复习备考、通篇画满笔记的这本著作,至今仍摆在我书架的显眼位置。而引领我进入复旦的“贵人”是吴心伯老师,他既是我学术道路、也是我人生道路的引路人。
二、 切问近思,学海探赜
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底蕴深厚、学术资源丰富、名师大家云集、学术规范严格, 对于像我这样求知若渴的学子而言,无疑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学术殿堂。我在这里尽情吮吸知识的甘露、徜徉知识的海洋,完成了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2006年5月与同学合影
浓郁深厚的学术氛围让我浸润熏陶、快速成长。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一经成立便是一座高地,真正是高点起步、高开高走。1985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争取到特定资源的支持,推动成立美国研究中心,并亲自兼任中心主任直至逝世。作为中国高校中最早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美研中心积攒、积聚了深厚的底蕴和优厚的资源,在中美关系、美国政治与外交、美国经济、美国社会与宗教文化、美国亚太战略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研究优势,很快就闻名于国际关系学界。早在2000年,美国研究中心就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美国研究的翘楚。在我读博时,美国研究中心建设再上新的台阶,学术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特别是每一位博导的研究都形成体系甚至自成一派,在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美国研究中心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走在前列,在推动中美交流、影响外交决策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美国研究中心在2017年被批准成为教育部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在多次第三方智库评价中都名列前茅。美国前总统卡特、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多位美国高官曾到访美国研究中心。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并举行座谈会,在与吴心伯教授对话时,提出著名的对台“三不政策”,给美国对台政策定了调,从中可见美国研究中心在中美关系实务界的影响。在我读博三年中,曾多次现场聆听中美政要、学术大咖出席的高级别对话,这些在美国研究中心算是很平常的交流活动,在我离开复旦之后再也很少有机会参加了。另外,美国研究中心提供的硬件资源也是一流的,8000平方米的办公大楼、3万余册的外文原版图书,如此条件放眼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正是这样优渥的学术资源和环境,熏陶了我的学术意识,耳濡目染间锻炼了我的学术素养,研究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2006年5月与外教Shelley Rigger开展研讨
名师领衔的授课体系让我茅塞顿开、拨云见日。复旦国关院的学业压力远比我预想的要大。记得刚开学不久,我到吴心伯老师办公室报到,想请吴老师开一个阅读书单,吴老师则说:“你先把课上好!”等到一开课,我才明白吴老师此话的深意。复旦的专业课程设置及老师们的授课,体现了自由开放而又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和治学精神,课程不算太多,但要求都很严格,学习过程还是比较辛苦的。给我们开课的老师几乎都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教授,他们授课方式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逻辑思维训练和独立批判性思考。印象最深的是曹沛霖老师给我们上“比较政治制度”课程,那时曹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但在课堂上仍然精神矍铄、逻辑缜密、思路开阔,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原理提炼和制度分析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在讲完每个专题后,还特别进行理论总结和反思,让我们收获满满,我们也为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坚守所敬佩、感动。倪世雄老师给我们上“比较国际关系理论”课程,不仅要求我们大量阅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更要求我们用中国思维、中国立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扬弃,前瞻性提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与今天大力推进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异曲同工。吴心伯老师教授“美国亚太政策”课程,特别重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他每节课都要求学生作重点发言,给我布置的题目是“冷战终结前后美国对日政策大辩论”。我花了一整个星期准备发言提纲,发言后得到吴老师的即时评价和点拨。虽然准备过程比较辛苦,但学术归纳和分析能力得到较快提升。除了学分课程外,我还旁听了其他老师的一些课程,如林尚立老师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沈丁立老师的“国际安全研究”、石源华老师的“朝鲜问题研究”、朱明权老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徐以骅老师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等,这些课程都有比较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它们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启发了我的逻辑思维,让我终身受益。

2008年1月在校园北区食堂前留影
名导严师的学术教导让我系统提升、学有所成。吴心伯老师指导学生之严格在国政学圈是出了名的,不少学生既仰望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但又怯于他的严格要求而不敢报考。像我这样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能拜于吴老师门下,是何其荣幸!也正是吴老师的悉心指导,才使我顺利完成学业、正式踏上学术之路。对于博士生而言,论文选题无疑是一个比较难过的门槛,选题之前要做大量的文献综述和论证,要紧跟学术前沿、抓准学术脉搏,还须得到导师的认可,仅仅这个环节就让不少博士生“痛苦”不已。而我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吴老师直接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2006年朝核危机正酣,中国在北京主持“六方会谈”,中美等国围绕朝核危机正进行台前台后的利益博弈。善于把握中美战略大势的吴老师对我说,你就写“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互动”吧,我问: 该如何把握这个选题的要点呢?吴老师用他一贯简洁而有力的语气说: 一要把握中美战略的本质;二要把两国的“互动”写出来;三要有历史感,把历史脉络梳理清楚。言简意赅的几句话,成了我开题和写作的指导思想。在指导论文方面,吴老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严”。吴老师的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比如他采取“逐章指导法”,让学生每写完一章就及时发给他,他会打印出来仔细批阅,对其中的逻辑观点、论证方式、语言表达、参考文献,甚至标点符号等,都会进行认真修改,待我们修改并达到他的要求后,才能接着写下一章。这种极其严格而又细致的指导方式,让我们既惊叹又感动。二是“实”。吴老师常以“做学问,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激励我们,主张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论文既要有学术逻辑,也要有政策逻辑,不能为理论而理论,而要能够经世致用、解决现实问题。三是“新”。吴老师对论文创新的要求非常高。他注重研究范式创新和知识结构更新,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独立思考和创新写作的能力。在吴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科学指导下,我的论文写作过程既艰辛又顺利:“严”让我丝毫不敢懈怠,吴老师严格的“过程把控”让我写作中少走了不少弯路;“实”让我胸有成竹,按照吴老师“问题导向”的指引,紧扣中美战略、互动、政策等关键词进行史料梳理和论证,厘清了逻辑架构和论证方式;“新”让我豁然开朗,我遵循吴老师“研究范式创新”的引导,构建了一个“互动”理论,以三种互动模式分析了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互动的演变历程,这种研究范式至少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颖的,得到评阅、答辩专家的积极评价。正是吴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把关,才使得我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评当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三、 拾级而上,饮水思源
从复旦毕业后,我来到位于“天府之国”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教师,顺利评上副高、正高,获聘博士生导师,又先后在学院和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同时,我的生活也稳定下来,算是在成都扎下了根,对于现状已很知足。回望在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三年求学经历,我时常想: 如果不是在复旦这三年,经这所名校的“认证”,我能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吗?吴老师经常跟学生提及“学有所得、处事有方、为人有道”的理念,我就用这三句话概括一下毕业后的工作实践和一些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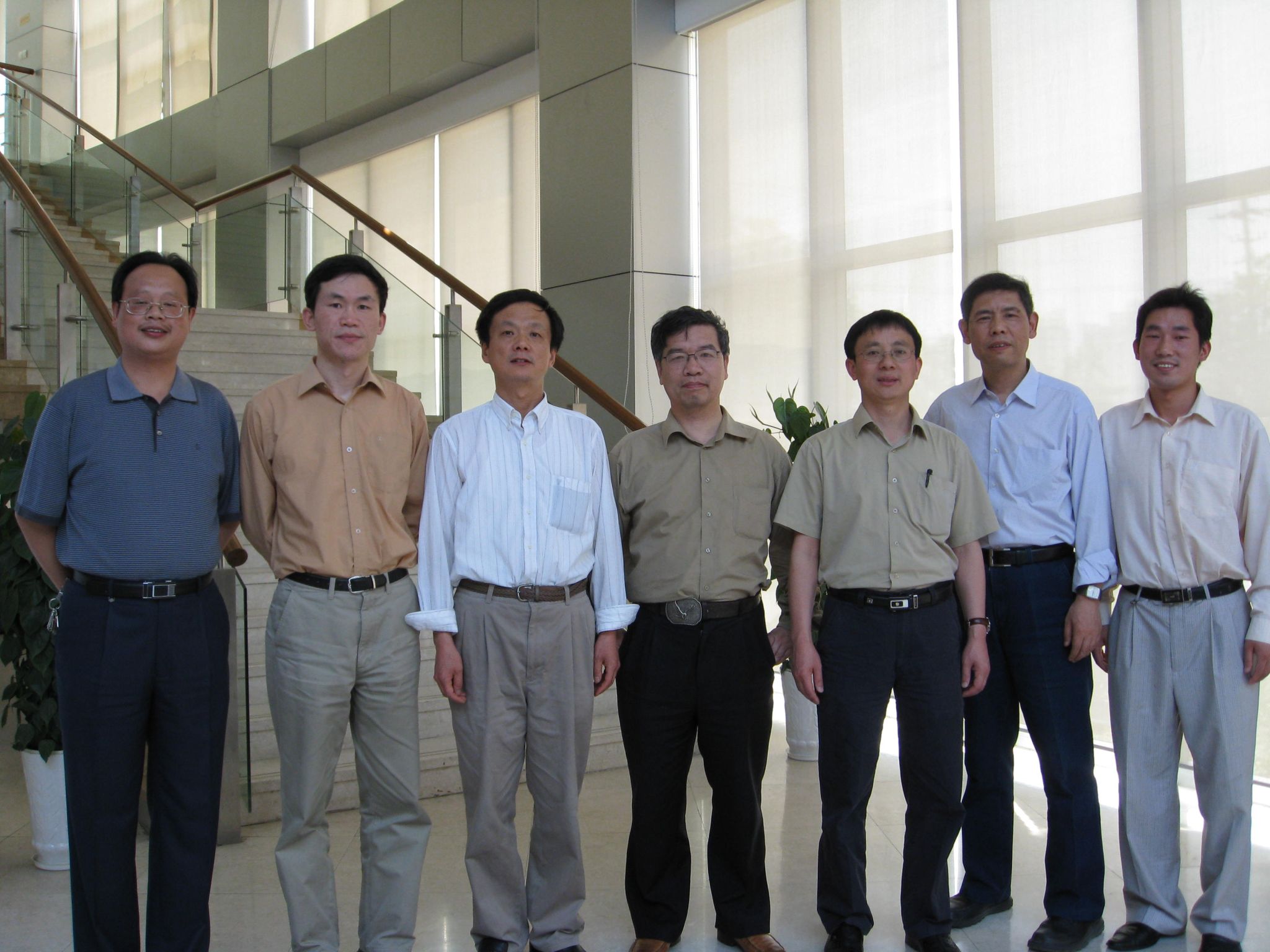
2008年5月学位论文答辩后与导师吴心伯等合影
一是学有所得。美国研究中心给我的学术熏陶和训练让我至今受益。来到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后,我的研究方向转向党建、思政等领域,同时关注教学研究。虽然研究领域变了,但我在复旦养成的学术习惯、思维方式和学到的研究方法等,给了我做研究的“捷径”,特别是吴老师教导的要有历史深度、战略高度、现实关联度,以及他的简洁而富于逻辑的思维方法,已经深入我的脑海,成为我一以贯之的研究指引。说来也巧,西南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一样也有座光华楼,“光华”同样取自《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西南财经大学的校史最早可追溯至1925年6月脱离上海圣约翰大学而成立的光华大学,1938年,光华大学因抗战而迁到成都,成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后经分设、合并、更名,才有了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的“经世济民、孜孜以求”大学精神,与吴心伯老师倡导的“经世致用”内涵高度一致。所以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感受到的文化历史氛围,与在复旦美国研究中心时的熏陶所感是相通的。这既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历史缘分吧。
二是处事有方。在我印象中,美国研究中心的老师既是学术领军人物,更是为人处世的表率,尤其让人感受深刻的是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学者风骨与师者风范,比如倪世雄老师的求真和通达、吴心伯老师的严谨和干练,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始终坚持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每写一篇文章都仔细斟酌、反复修改,每上一堂课都认真备课、一丝不苟,每办一件事都不折不扣、慎终如始。美国研究中心教给我的不仅是学术之道,更是处事之道,它让我有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事之方,我的事业也因而比较平顺。
三是为人有道。“三分做事,七分做人”,做人与做事的道理是相通的。美国研究中心教给我的为人之道,值得我一辈子珍惜并经常运用,尤其是吴老师为人处世的智慧,对我影响深远。吴老师对学生除了“严格”,更多是“仁爱”,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他会针对不同学生的特长、特点而采取针对性指导和帮助,比如为英文较好的学生争取国际交流机会,为潜心问学的学生提供学术资源。他知道我出身农村、经济条件不太好,便推荐我申报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提供的“韩国学奖学金”,连续两年的资助让我摆脱了生活之忧,使我能够专心致志按时完成学业。即使我到成都工作之后,吴老师还时不时发信息问我近况如何,让我深受感动。在吴老师影响下,我始终保持一颗真诚、质朴之心,与学生打成一片,从学习和生活上都尽量给予他们关怀;与同事坦诚相待、相互支持,在团队建设中维持团结友爱的氛围。为人之道与为学之道相互融通、相得益彰。

2008年6月在复旦大门前毕业留影
时间一晃,我离开复旦已经17年了。虽然身份变了、环境变了,但我对美国研究中心给予我破茧成蝶机会的感激之情始终没有变,对师长们给予我教诲、帮助我成长的感恩之情始终没有变。无论何时、身处何地,我都会将这份感恩感激之情置于心间,让时光来篆刻这份永不褪色的情怀。
谨以拙文献礼美国研究中心四十华诞,衷心祝愿美国研究中心未来更执学术牛耳,以智慧之光铸就思想的灯塔!祝愿美国研究中心的师长学术之树长青,继续书写美国研究高地的辉煌!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5级博士研究生 陈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