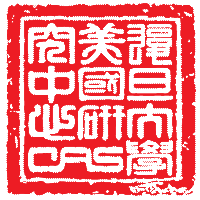2025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迎来了四十华诞。我从1992年入职中心至今,已逾卅载。这三十多年里,中心从砥砺初创到崛起为享誉海内外的美国研究学术重镇,我个人也从初出茅庐的博士毕业生成长为复旦大学的一名骨干教师。回首这段峥嵘岁月,许多鲜活的记忆涌上心头,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就像一颗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连成一串,映照着这似水年华。
01 前辈的关爱与支持
我于1992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导师是汪熙教授。汪先生本来希望将我留在历史系工作,未果,于是将我推荐到美国研究中心,得到中心主任谢希德校长(那时她已卸任校长职务)和校外办主任卢义民老师的支持。不巧的是,几个月前中心刚进了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因此学校人事处不同意短期内中心再进人。多亏汪先生积极争取,并得到谢校长和分管干部人事的校党委副书记宗有恒老师的支持,此事才算敲定。正式入职之前,汪先生把我叫到他家,向我详细介绍了中心的情况,一一交代工作需要注意的事项,并郑重叮嘱道:“我可是在谢校长面前拍了胸脯,说你确实很优秀的,你可要好好干!”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没忘记这句话。

图|1992年4月,吴心伯与导师汪熙(左)在博士学位证书颁发仪式上
入职之前,我没有去美国学习的经历,作为一个专业的美国研究者,必须尽快补上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空白。汪熙先生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在外办主任卢义民老师的支持下,我入选了美国“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Asia, PISA)”的访问学者项目,于1994年1月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十个月的访问研究。赴美前的一天,上海雪后初晴,天气寒冷,谢校长专门来到中心,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吴心伯明天要去美国了,祝他一切顺利,我们希望一年后在中心欢迎他回来。”在此之前,中心派了一些青年教师赴美深造,但大多都没回来,谢校长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提醒我访美要如期归来,为中心效力。老人家良苦用心如此!
出国之前,汪先生把我叫到家中,交代赴美学习生活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告诉我美国冬天室内都有暖气,厚衣服不必带的太多,衬衫要多带一些,等等。还给我访学的指导老师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何汉理)修书一封,请他多关照。汪先生特别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的出版问题。由于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未能赴美搜集一手的档案材料,他叮嘱我赴美后一定要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搜集补充原始资料,修改博士论文并出版。带着汪先生的嘱咐,我在美期间花了两个月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补充,于1997年作为汪先生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16辑出版,这也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
1997年7月,为配合江泽民主席访美,我与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合作,在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中美第二轨道战略对话”的研讨会,深入探讨如何改善与发展中美关系,来自中美两国的知名学者如王缉思、张蕴岭、哈里·哈丁等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组织国际会议,筹备工作并不容易,幸亏身为中心主任的谢校长给予了大力支持。她不仅全程出席了对话,还主持了欢迎晚宴。我印象中谢校长很少全程出席中心召开的会议,一般都是开幕式致辞并合影后就离会。这次全程参与,不仅体现了她对这个重要议题的高度关注,也是对我个人的莫大支持。会后,在时任市外办主任周明伟老师的安排下,汪道涵老市长还会见了美方代表,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这次会议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哈里·哈丁高度评价道:“这是我过去20年在中国参加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最好的研讨会。”没有谢校长的大力支持,会议不能可如此成功。

图|1997年7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合作举办中美第二轨道战略对话,前排右四为谢希德校长,前排右三为吴心伯
02 亲历重要来访
中心既是美国研究的重镇,也是对美交流的重要窗口。在中心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我或参与或主持与诸多美国政要的交流对话,其中几次活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是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这是对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的回访,也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美方对克林顿访华的一个定位,就是要向美国公众展示一个快速发展与变化的中国。为此目的,在访问上海期间,美方安排了一场克林顿夫妇主持的座谈会,主题就是“构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邀请十来位上海法律界、教育界、文艺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我和中心主任谢希德都在受邀之列。记得座谈会之前,时任上海市外办主任周明伟老师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参加座谈会的相关事宜。会后,他又把我单独留下叮嘱了一番,大意是我作为参会的唯一一位中美关系学者,要有政策敏感性,注意临场发挥。6月30日上午于上海图书馆一楼大厅举行的这场座谈会,除了应邀参加的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外,还有美方访华代表团的所有成员以及中方陪同人员,报道克林顿访华的中外媒体则齐聚二楼走廊,“围观”这一重要活动。座谈会是在半开放的空间举行的,总体气氛比较轻松。

图|1998年6月30日,吴心伯应邀参加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座谈会并受到克林顿总统的接见
座谈会开始后,克林顿总统先与教育、宗教、文艺等领域的代表进行交流,第一夫人希拉里也活跃地加入对话。我是最后一位被提问的。在此之前,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克林顿总统对我提问之前,坐在旁边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Sandy Berg)给他递了一个条子,克林顿看后扫了我一眼,就开始向我发问。他先问了我一个个人问题:“吴教授,我来自美国的阿肯色州,从你的背景看,你来自中国的阿肯色州(安徽省),然后你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读书和执教,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成长经历?”我知道他的这个问题是想让美国公众了解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我简单介绍了自己作为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如何通过高考进入复旦大学,在国家助学金的支持下完成学业,并成为复旦大学一名教师的经历,强调当下中国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流动性增加,个人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接着他话题一转,问我如何看待这几年的中美关系,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何看法。我谈了这几年中美关系所经历的曲折和改善,强调美方处理好台湾问题是关键。克林顿表示同意我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并声称: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这一表态引起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政策宣示。
此后我去华盛顿访问,了解到克林顿是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飞机上决定要公开重申“三不”政策的。在此之前,克林顿曾经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方做过类似的承诺,但中方希望他在访华期间在一个公开场合做相关政策宣示,这是克林顿访华中方最希望取得的成果。然而克林顿在访问西安、北京时都没有就此表态,最后他在上海的座谈会上公开宣示美国对台“三不”政策,满足了中方的期待。鉴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特别是1995年李登辉窜访美国所导致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紧张,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期间公开明确美国对台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我个人能够亲身经历这一重大外交事件,深感荣幸。
第二件事是2001年拜登来访。2001年初夏我赴华盛顿访问,见到老朋友季浩丰(Frank Jannuzi),他那时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拜登的助手,负责东亚事务。他告诉我,拜登参议员即将访华,计划访问上海、北京,拜登对与青年人的交流特别感兴趣,有没有可能造访复旦大学并与学生见面?我告诉季浩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将很愿意接待拜登一行。8月7日上午,拜登和其他三位参议员以及助手季浩丰一行造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校领导与他们一行礼节性会见后,就来到一间大教室与中心师生交流。按照事先敲定的活动安排,四位来访的参议员每人先谈15分钟,然后跟大家互动。拜登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第一个发言,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他主要谈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中国未来的展望,相信中国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第二是台湾问题。他表示,此行先到台湾,因为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有安全关切,同时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两岸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当时正值小布什执政初期,奉行亲台政策,小布什本人曾公开表示美国将“竭尽所能防卫台湾”。拜登强调,美国同台湾之间没有防务条约使美国承担防卫台湾的义务,因此小布什的表述是错误的。拜登还告诉大家,他在台北见到陈水扁时告诉他,台湾如果搞独立,将自己承担责任。第三是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他谈到美国要以外交和谈判的手段处理朝鲜的导弹计划,并谈到与俄罗斯谈判修改《反导条约》,并谋求在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保持透明度,强调该计划不针对中国等。我在座谈会结束后问拜登,这是不是他第一次访华,他颇显自豪地告诉我,他1979年就来中国访问,还见过邓小平。
第三件事是2009年奥巴马访华。奥巴马执政之初,美国深陷金融危机,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因此特别重视对华关系。他决定在2009年11月访华,成为中美建交以来首个执政初年就正式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之行的首站是上海,其中一档活动就是于11月16日下午在浦东科技馆与来自复旦等几所大学的青年人交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主持他的演讲。在此之前,学校要我给参加此次活动的复旦和其他高校的学生介绍美国与中美关系的相关情况,让大家做好交流准备。16日下午的活动,我和美国研究中心的几位老师一道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参加。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让大家充满好奇。这次近距离的观察,给我留下几点印象。其一是奥巴马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持比较积极的观点。与一些美国政界人士习惯于对华说教不同,奥巴马的演讲显示出其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尊重和对中美合作的期待。其二是奥巴马对国际事务持比较进步的观点。与他的前任小布什穷兵黩武、奉行单边主义不一样的是,奥巴马更注重推进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其三是作风亲民。活动结束后,他一边向听众挥手告别,一边朝大厅出口处走,这时前排的几位同学向他伸出手来,他立即停下脚步跟他们握手,于是更多的同学伸手待握,这时奥巴马没有扬长而去,而是折转身往回走,跟前排同学们握了一圈手,这才挥手作别。看得出来,奥巴马很享受中国大学生的热情,他的亲民作风无疑也是美国选举政治文化给熏陶出来的。
第四件事是基辛格博士来访。2013年7月2日,90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在复旦校友、前任国务委员唐家璇的陪同下来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师生交流,我作为中心主任参加了杨玉良校长同他的会见,并主持随后的师生交流活动。虽然我之前在一些场合也见过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此次是近距离接触,印象更加深刻。基辛格在交流中自称是新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每个国家在践行民主理念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国不应该使用武力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在谈到其人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时刻时,他提到二战前在德国遭受的迫害,二战期间重返德国见证德意志帝国的崩溃,更提到他的在华经历,目睹中国文明的伟大创造,感受中国人深重的历史感。在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的问题上,基辛格认为即便中国GDP总量赶上美国,中国的人均产值还是要落后很多。不过他指出,在他20世纪70年代会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时,中国国力要弱小很多,但是中国领导人依然展现出强烈的自信。对于中国的崛起,基辛格认为美国人应该更努力地工作、更有效率,把自己国家建设得更好。他表示,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难以置信,但美国并没有衰落,决定中美两国竞争的关键因素是谁更有能力创新,而中国创新不足。他还强调,中美两国谁都不能强加于人,两国都不能从对抗中获益。基辛格不无自豪地透露,他认识尼克松以来的10位美国总统,与他们每个人都交流过,讨论如何推进中美关系。在谈及对不同时代的青年的印象时,他认为读纸质书长大的人大多喜欢思考,思想有深度,而互联网一代获得信息多,但比较肤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时,基辛格言简意赅,话不多,但非常精炼到位,体现出基辛格式的智慧。老人家很喜欢跟年轻人互动,原定一个小时的交流最后延长了近半个小时才结束。

图|2013年7月2日,吴心伯与基辛格博士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影
第五件事是美国前总统卡特来访。2013年11月11—12日,我应邀出席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的“中美关系论坛”,首次见到在其任期内与中国建交的卡特总统。当时他已是89岁高龄,但精神矍铄。由于卡特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贡献,与会的中国代表都争先恐后要跟他握手合影,卡特总统善解人意,慷慨地表示愿意与每位中方与会者合影,于是当天下午卡特中心安排我们中方代表一一与卡特总统合影。我拿到与卡特总统的合影感到很开心,同时又为这位中美建交的决策者尚未到访过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而感到遗憾。2014年初,我得知卡特总统当年晚些时候要访华,于是就与卡特中心刘亚伟博士联系,邀请卡特总统来访,此事得到时任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杨玉良的大力支持,顺利落实。
2014年9月9日上午,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夫人一行应邀到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杨玉良校长在贵宾室会见卡特总统夫妇,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可能是为了感谢我安排此次活动,卡特总统赠送我一本刚刚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他亲笔签名的著作——《她们的世界——来自卡特总统的疾呼》中文版。随后,卡特总统在中心报告厅围绕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卡特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看待这对关系要用历史眼光,当下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并非新问题,实际上从来就有,不应夸大有关问题的影响,从而伤害中美关系。卡特主张看待中美关系还要有宽广的胸怀。他引用习近平主席关于“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话语进一步表示,太平洋不仅足以包容中美关系,也足以容纳发展好中美两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在演讲中,卡特多次回忆他和邓小平共同决定并推动中美建交的历史过往,特别强调他和邓小平都认为中美友好与合作将确保世界和亚洲的繁荣与和平。他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1978年7月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博士一行访华期间,邓小平在会见美方代表团时提出要派5000名中国学生赴美学习,于是普雷斯半夜给他打来电话请示如何答复中方,卡特果断地说:“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来!”听到这一精彩分享,现场师生掌声雷动。尽管已有90岁高龄,但卡特演讲中依然思维清晰、逻辑严谨。演讲结束后他与师生积极互动。在回答关于如何面对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新挑战时,他特别强调两国青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卡特欢迎在座的所有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并特别推荐了自己的家乡佐治亚州。在离开会场前,卡特总统夫妇特地走到观众席前,与前排学生一一握手话别。在卡特夫妇的见证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卡特中心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这是卡特总统最后一次访华,我很高兴他在生前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中到访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图|2014年9月9日,吴心伯与卡特总统及夫人罗莎琳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影
03 大洋彼岸的亦师亦友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结识了不少美国朋友,其中一些于我而言亦师亦友,与他们的交往不仅极大地裨益我的研究工作,也令我收获了珍贵的跨国友谊。限于篇幅,这里略述其中几位。
首先想到的是哈里·哈丁教授,他是我1994年赴美访问研究的指导老师,时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部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的负责人。记得他1993年7月来华面试“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访问学者项目的申请者,我有幸入选,并获得了赴华盛顿跟他从事研究的机会。那时哈丁是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年富力强,风头正健,能够在他的指导下工作确实机会难得。我1994年1月赴美时,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和一门本科生课程,我旁听了这两门课,他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令人印象深刻,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不少启迪。那时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和东欧剧变的冲击,中美关系处在不正常状态,美国对华舆论环境很不友好,但难得的是哈丁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持比较客观公允的立场。当时我研究的课题是“冷战后的美国亚洲安全政策”,哈丁给我推荐了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章,但我觉得光阅读文献还不够,希望访谈一些美方专家学者,他深以为然,给我开列了一个美国专家学者和前政府官员的名单,并给他们一一写信介绍我。我按图索骥,在华盛顿、纽约和波士顿访谈了名单上的绝大部分专家学者,这对我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在此基础上我顺利完成了研究报告,哈丁将其推荐给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东北亚研究》杂志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它增强了我用英文写作论文的兴趣和信心。1995年初结束访问研究回国后,我与哈丁一直保持联系,他推荐初出茅庐的我参加了不少研究项目和会议,使我获得宝贵的学术交流机会,他也积极支持我举办的一些中美关系研讨会。从个人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哈丁教授无疑是对我帮助最大的美国学者。

图|1996年6月,吴心伯与何汉理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影
其次是迈克·奥克森伯格(Mike Oksenberg)。他是20世纪7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卡特政府时期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卡特总统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赏识。1996年6月,以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为团长的美国人大会(American Assembly)代表团访问中心,围绕“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与中方学者进行了研讨,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奥克森伯格也是美方代表团成员。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午餐时他和我坐在一起,跟我聊个不停,临走时告诉我,他在主持一个研究冷战后美国东北亚同盟体系的项目,希望邀请我参加。这年8月,我应邀到斯坦福参加项目会议。这是一个为期三年(1996—1998年)的研究项目,每年在斯坦福开会一次,其中1997年我还在斯坦福访学两个月。记得那年感恩节,奥克森伯格邀请我到他家共进晚餐,问到我老家安徽省岳西县的情况,他表示很想去看看。奥克森伯格告诉我,他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和治理很感兴趣,参加了一个山东邹平的乡村研究项目,但还没有去过安徽。于是翌年5月,我陪同奥克森伯格及其夫人一起去了安徽岳西,见到我仍生活在老家农村的父母和兄弟、姐姐等家人,在我老家吃了午饭,在村子里四处溜达,还与县领导进行了交流。这次安徽之行给奥克森伯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那几年,我与奥克森伯格联系较多,对这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也有了更多地了解。他曾告诉我,他小时候在美国农村长大,他父亲每天喜欢问他的一句话就是:“你吃饱了吗?马喂了吗?”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一直关注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他对大学时听说毛泽东致力于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和改善农民的生活,于是便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20世纪80年代末,经中国民政部门批准,他参与了一个对山东邹平的乡村研究项目,多次去那里进行调研,还在1997年陪卡特总统去过一次。奥克森伯格对国际事务有独到的看法。有一次他告诉我,苏联解体时,很多美国人欣喜若狂,而他私下却不以为然,觉得单极取代两极,美国缺少外部制衡力量,世界可能会更加不稳定。奥克森伯格亦学亦官,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就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而言,他教给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可惜的是,他2001年初因病去世,年仅62岁。中国失去了一位为中美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朋友,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良师。

图|1998年8月,吴心伯与奥克森伯格(左二)、佐利克(右一)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合影
第三位是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我跟他也是在1996年6月美国人大会代表团来访复旦美研中心的那次研讨会上认识的。此后不久,我去哈佛访问,他对我的来访很高兴,在哈佛教师俱乐部安排了晚餐,邀请费正清中心的一些老师参加,热情地向他们介绍我。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不时在上海、波士顿、华盛顿、北京等地见面。2006年我申请美国和平研究所杰宁斯·兰多夫(Jennings Randolph)高级研究员,他给我写了推荐信。2018年是我们线下互动的最后一年。这年4月,傅教授邀请我赴哈佛费正清中心作学术报告,他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头天晚上,他邀请我和哈佛的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在他家共进晚餐,大家一边吃着从附近中国餐馆叫来的外卖,一边聊着中国和中美关系,气氛非常好。12月,傅教授应我的邀请来沪参加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上海市对外友协共同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研讨会,会前的一天(12月12日)到复旦美研中心发表题为“中美关系四十年的思考”的演讲。当时中美关系因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而趋紧,大家都很关心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我陪同傅教授走进演讲教室时,发现里面早已座无虚席,地上都坐满了人,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看到这个场面,傅高义教授显得非常开心,他出乎意料地宣布:“今天报告全程讲中文”,热烈的掌声再次爆发。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傅高义基于自身的研究体会和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美关系40年发展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也坦率地表达了他对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担忧。演讲结束后,他又耐心地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十几个问题。2020年11月美国大选揭晓后,我和傅教授同时出席了一个线上研讨会,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此后不久,就获悉他去世的消息,那时的心情只能用“震惊”和“不舍”来形容。

图|2018年12月,吴心伯主持傅高义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演讲
傅高义教授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80年代曾到广东从事半年多的考察,研究广东的改革开放,2000年退休后倾注十年心血写成《邓小平时代》。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但他对中国的兴趣和投入远远超过日本。他研究中国不是从美国的经验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傅高义经常说,治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因此他特别注重研究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来设计制度、制定发展战略,这使他能够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治理与发展,而非从美国的视角对中国评头论足。此外,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与中国学者交往,注意倾听中国学者的见解,虚心地交换意见。
最后一位要提及的是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博士。他先后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在美国政界和商界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对华工作经历,对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观察。我与他初次见面是1998年夏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的一次研讨会上,经奥克森伯格教授的介绍而认识,那时他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总裁。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很谈得来。记得2000年我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的时候,他加入了小布什的竞选班子,有一次见面他向我介绍了共和党竞选纲领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2000年大选后,他加入小布什政府,先后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常务副国务卿,而后又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段时间我们基本没有联系。
再次见面是2013年5月,我邀请他来复旦出席“上海论坛”,5月25日那天他和我在美国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场关于中美关系的对话。在对话中,佐利克博士回顾了他与中国初次接触的经历,谈到了他对中国的印象和对中国政府官员的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他对中国发展的一些建议,也介绍了他担任常务副国务卿时主持与中国的高层对话的情况。那次我请他到我家吃晚饭,饭前我们在小区散步聊了很久。此后我去华盛顿访问也多次去拜访他,他也乐于接待我。佐利克是个健谈的人,他熟悉美国政治和体制的运作,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地跟踪和深入地思考,有历史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每次跟他交谈我都颇有收获。2025年3月,他再次来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为他的著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America in the World: A History of U.S.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中文版举行发布会。这本书是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它以全景式故事叙述的方式,聚焦从美国建国到21世纪的外交思想、实践和传统,提炼了以北美基本盘、自由贸易、同盟、国内政治支持以及国家使命感为特征的五大外交传统。佐利克对此书中文版的问世感到欣慰,那天与听众的交流也很热烈,然而在特朗普归来的背景下,他作为一位传统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言谈之中对美国与国际事务的未来变化透露着深深的忧虑。
04 结 语
岁月如梭,记忆如金。对往事的珍贵记忆使人不忘来时路,不迷失前进的方向。回眸过去卅载,我深深庆幸能够加盟中心这样卓越的发展平台,更庆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与进步为美国研究中心,也为个人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站在中心四十华诞这个历史性的节点,面对新形势赋予我们的新使命,作为美国研究的国家队,我和中心同仁深感责任重大,唯有勇于担当,勠力前行,才能不辜负先辈的殷切期待,不负国家重托,谱写中心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