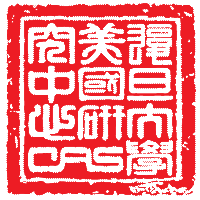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4/20011225/634544.html
冷战:美国制造
“冷战”一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是指“二战”后东西方阵营之间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除直接军事交战以外,一切敌对行动的总称: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核恐怖下的势力均衡、两极之间的紧张对峙……它既不能被称为战争,因为它争而不战;也不能被称为和平,因为它既不平也不和。于是,有人称之为“战争与和平的私生子”。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断定俄罗斯民族具有扩张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癖好,主张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以阻止其影响的扩大。这样,美国决策者以黑白分明式的宗教思维为指导,对苏联发动了冷战。
1946年初,美国政治家斯沃普在为参议员巴鲁克起草的一篇演说稿中首先提出“冷战”一词;1947年9月,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出版《冷战》一书,从此该词被广泛采用。而“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等一系列举措,最终将“冷战”一步步变为现实,形成了在心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全面对抗,构成了冷战的丰富内涵。
因此,冷战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战争,它是一种特殊的阵营对抗形式,这种对抗形式亘古未有,“人类历史上也只有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对抗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基辛格说得好:“超级大国的行为往往像两个全副武装的盲人在一间屋子里摸着找路。每一个人都认为对方使自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他认为对方能够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变化不定、妥协、前后不一,才是决策的本质。但屋里的每一方都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始终如一的、有远见的和一贯的。于是,时间长了,就是两个盲人也能造成巨大的伤害,更不用说给屋子带来的损失了。”
屋子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与此同时盲人却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升级为一种强制地把对方联系在一起的、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真正的原则分歧、实在的和想象的利益冲突、大量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理解和蛊惑人心的宣传又加速了这种局势的发展。每个超级大国采取它真诚地认为是出于防御目的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又被对方认真地视作不能接受的威胁,必须采取坚决的对抗措施;每一方都不断地使对方确信其担心是有道理的;每一方都受这样一种倾向的支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局部的冲突,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斗争,用绝对化的观点来看待相对的分歧。于是,双方步调一致地扩大了冷战的范围。
这就应了埃默森的一句话:“在分析历史时,切忌过于复杂深刻,因为起因往往很简单。”正因为如此,冷战的突然终结出乎世界的意料,也就不足为奇了。
冷战的终结是以一连串的事件为标志的: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统一、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然而,其中最本质的还是作为一种价值标准的终结。
冷战价值标准的终结
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利益的冲突,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相互摩擦和过度反应,这一切聚合在旧世界格局向新世界格局转化之际,引发了“冷战”。随后,意识形态与价值标准的严重对抗,产生了“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错觉,人类的价值标准还从来没有陷入如此不能自拔的困境。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彻底埋葬了冷战的价值标准,弥合了分裂的世界。人类逐渐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人类无东西方之分”。西方对冷战的终结普遍抱有一种盲目的乐观,纷纷断定“民主赢得了东西方之间的一场争论;市场赢得了经济上的争论”,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历史的终结”时期,“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应运而生。至此,冷战的“价值标准”才真正有了转化和继承。
然而,“价值标准”从来是胜利者的托词。现实主义一针见血指出,冷战不过是美国制造出来的谎言,隐藏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背后的仍然是古老的权力游戏,只不过这种游戏带上了意识形态的时代色彩。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指出:“根据冷战的言论,世界的根本分裂是资本主义和不信神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从利害关系的大小和斗争的力量来看,意识形态在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中都从属于利益,这两国的行为与其说是像救世主领导人的行为,不如说是传统大国的行为。”
美国本身对言辞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视而不见。其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当追求权力与追求法则不冲突时,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装点上自由主义,而无需讨论根本的权力事实。事实上,美国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并非源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源于现实主义原因,但却与自由主义法则相一致,因而,决策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当成意识形态冲突推销给了公众。
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条款)》。可是,当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与苏联联合抗击德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这一美国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原始民主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
反恐战争:美国标准的再现
1999年5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特别报道《一个纷争的世界》的观点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美国行政当局正面临着不久将被思想库称为E2CW(即“冷战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的挑战。
作者并未给出详细分析,但断定,美国主导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形成:“十年来,世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一直是由西方对苏联的胜利塑造出来的。自1989年以来,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美国的实力水平。只有美国才拥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相结合的优势————硅谷、隐形轰炸机和‘星球大战’计划,全都融为一种能够确定全球议程的力量。”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的骇世之作彻底埋葬了种种犹豫,“冷战”一词要么得以抛弃,要么得以转化————总之,世界宣告了冷战后时代的终结。
有舆论将“9·11”事件后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定义为“第二次冷战”。布什更是宣扬恐怖分子是出于对世界自由灯塔的怨恨甚至忌妒而袭击美国,并提出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分子也是恐怖主义行为”的布什主义,明确警告“中立是不公正的”。这令人想起冷战斗士、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那句广为传诵的话———“中立是不道德的”。
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冷战时期那种“黑白分明”的逻辑。人们不自觉地发现,国际社会从冷战时期的“美国制造”进入到了当今时代的“美国标准”时期。
美国总以美国观来定义时代,并左右国际社会的视线。美国霸权的继续,得益于美国能不断更新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内涵使之包容新力量,抑制可能的破坏力量。这次也不例外,基辛格称,现在是“清除冷战后遗症(国家处于敌对关系),重塑国家间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绝好时期;各国利益正趋于一致,具有(反国际恐怖主义)共同目标。
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怖主义战争的迅速取胜,无疑更强化了美国单极霸权的地位及其意志。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一度迷惑了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特征,也埋下了非对称冲突的种子。恐怖主义9月11日的暴行,其实就是在无法与美国进行常规交锋的非对称冲突下,采取的极端手段。
当前的时代是单极霸权与非对称性冲突相交织的时代,前者是由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带来的,后者则由“9·11”事件揭开序幕。正是在这一时代转折时期和国际背景下,我们来纪念前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