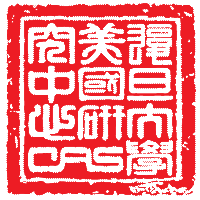http://column.huanqiu.com/wangyiwei/2008-01/48528.html
未来几年,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和转型期,不论谁将赢得2008年大选,都难以彻底改变美国的处境。于是,有人称美国处于战略拐点。其实,是美国战略的内涵在变化。传统美国大战略是基于常态,着眼于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突变,思考的问题是:“有怎样的战略目标”、“用什么战略手段能够实现”、“谁会在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构成挑战”、“实现目标的战略环境如何”,等等;现今美国战略,是基于非常态,被现实所束缚和影响,被动性不断增加。更本质地说,认识美国霸权兴衰和美国战略走向的关键,就要先理解“世界是否能容忍美国霸权”(空间上的概念)和“美国霸权战略能持续多久”(时间上的概念)。
世界越来越难以容纳美国霸权,美国霸权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
大国战略都要面临空间与时间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从空间概念上看,世界越来越难以容纳美国霸权。表现之一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传统霸权均势战略构成切实挑战。先前美国有学者提出“塑造有利于自由的均势”,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表现之二是传统大国矛盾限制了美国的自由度,导致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利益分化、竞争加剧。欧美在当前气候问题上的较量是典型例子。表现之三是美国无论打着“志愿者同盟”还是“民主同盟”旗号,都难以一呼百应,美国难以主导新的国际规范、秩序和体系,在刚刚结束的巴厘岛气候大会上,为巴厘岛路线图出笼让路就是明证。
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美国霸权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表现之一是全球化时代西方的衰落(西方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构成的“金砖四国”等的崛起为代表,证明世界不再是圆的,世界不可能永远围绕西方的圆心转。表现之二是虚拟经济的脆弱,全球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最近这一轮美元持续贬值,具有与历史上不同的意义,表明美国金融战略“寅吃卯粮”的弊端,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阶段,而次贷危机更是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过于依赖房地产消费市场的危险。表现之三是滥用美国力量的危害。美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招来天怒人恨,美国成了传统国际秩序的破坏者,直接导致反美主义成为全球性现象。
对此,美国的精英早有感知。遗憾的是,他们的反思囿于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美国是否应当来领导世界。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去年底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领导的跨党派的“聪明权力(smart power)”委员会,参照“软权力”、“硬权力”的模式,发表了《聪明权力报告》。他们虽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领导世界日益力不从心,但仍然执着于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指望能够更多地运用“聪明权力”,平衡“软权力”和“硬权力”,尽可能延长美国的霸权,塑造世界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但是,这种战略目标与当前美国的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聪明权力”报告是“小聪明、大糊涂”。
美国正在寻求霸权减负,即实行霸权的核心层面与边缘层面的剥离,保住核心霸权,让渡边缘霸权,试图拉着新兴崛起中大国支撑其核心霸权
美国“领导”世界,支柱是美元霸权及其附着的军事霸权。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驻纽约的国际经济主任本•斯太尔表示:“美国极其幸运,因为美元也是国际价值标准———如果这一作用消失,美国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也会随之消失。”他强调,通过拯救其他国家走出金融危机,美国能够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各国在金融危机中需要的是美元,这赋予了美国巨大的优势。”但是,美国寅吃卯粮,滥发美元的结局,是世界对美元信用及对美国的信任不断下降。截止2007年第三季度末,以美元持有的外汇储备百分比降至纪录低点63.8%。对于美国政府不断玩弄美元贬值游戏,赖掉美国欠下的巨额债务,缓解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同时导致石油等原材料大幅涨价,向世界美元持有者转嫁、输出通货膨胀,国际社会已怨声载道,美元不能无限期挟持世界经济。
就军事霸权而言,往往也是与美元霸权挂钩的。比如,美国与海湾产油国之间一系列不成文但明确的条例———这些产油国用美元为石油合同计价,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换取安全保障,由此巩固了美元作为全球领军货币的地位。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石油美元成为替代黄金的美元霸权的救命稻草。在东亚地区,以美国为核心的“辐辏” 结构,也表现为美元霸权与军事霸权的交易———“东亚国家出口商品到美国市场,美国出口安全到东亚。”
可惜,福兮祸所伏。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的结局,导致了相反的结局:美国不能引领全球化、不能代表西方、不能代表国际社会。比如,民主党热门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竟然威胁说,美国要退出WTO。在美国的大选鼓噪中,公平贸易代替了自由贸易,成为各候选人讨好选民的共同政治口号。
于是,重新界定美国领导权成为必然。代表性的观点是区分美国霸权的核心-边缘层次:核心是金融霸权、军事霸权,这是美国挟持世界经济与安全的两大支柱,边缘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外交》杂志今年第1期发表国际关系理论家伊肯伯里的文章“中国崛起与西方的未来”,认为“中国不仅仅面对美国。它面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一个开放、融合、以规则为基础、而且有着深厚政治基础的体系。”作者据此把21世纪的斗争定义为中国和一个复兴的西方体系之间的斗争。问题是,美国还能继续代表西方吗?围绕巴厘岛路线图的争论,本来应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但事实上在美国与欧盟间展开。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前国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纳芒就气愤地指出,“‘西方’一词往往掩饰的是接受对美国的某种隶属关系”。
美国人迟早会认识到,美国领导权并非一成不变。处于转型时期的美国霸权,正在寻求霸权减负,即实行霸权的核心层面与边缘层面的剥离,保住核心霸权,让渡边缘霸权,试图拉着新兴崛起中大国支撑其核心霸权,当然只是分享其成本而不能享受其好处,并且防止后者挑战其核心霸权。
对世界来说,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为不断衰落的美国霸权下的世界寻找新秩序
美国的战略处境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呢?正如第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题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应当在全球化背景下去考量中美关系。反思中国的外交战略,赢得、争取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为此,中国崛起并不是要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美国霸权,而是既要能够规避美国霸权带来的风险,对其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加以防范,又要能够学会和适应在现有的国际体制下生存、发展,并且寻找到中美关系的结合点。
因此,中国复兴根本不想,也不可能去分享美国的霸权。无论是美国的老牌盟国,还是包括俄巴印中“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谁也不可能成为未来支撑美国核心霸权的新支柱。未来的中美合作与博弈会在更大的全球化体系下进行,这存在广泛的利益重叠处和滋生摩擦的可能,最终将实现利益和摩擦两者的平衡,塑造中美和谐之关系。实际上,这也很可能是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特征。对世界来说,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如何在多边和双边的复杂博弈中,为一个不断衰落的美国霸权下的世界寻找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