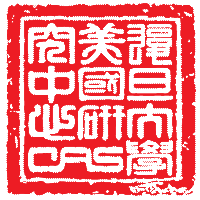美国的崛起发生在19世纪最后10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期,在这50余年间,美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建立了一套战后国际机制,缔结了一套控制欧亚的同盟体系,提出了处理世界事务的一套基本理念,这几大要素标志着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崛起。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美国崛起主要得益于内因,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它方便甚至加快了美国崛起的步伐。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美国没有一批强大而敌对的邻国,周围是相对弱势而友好的国家,美国军队中最重要的是海军不是陆军,因为打仗都是到海外去打。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周围是强邻环伺,或是一批虽然弱小却经常给你添乱的国家,那你的战略空间就会被压缩,资源就消耗在周边,就没办法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身手。这种安全的地缘环境是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美国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平台可以利用。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太平洋的利用受到限制;1914年运河开通以后,美国有了两洋平台,巴拿马运河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中美国最重要的海外战略资产。
其次是可利用的资源环境。这里讲的资源是人才资源。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美国吸收了全世界(主要是欧洲)到美国的2000万移民,另外二战前后又有大批犹太人到了美国,这对美国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难以用数字描述的。没有这样一批外部人力资源的注入,美国的科技优势就难以体现出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
第三是有利的人缘环境。美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成功地实现权力和平转移、霸权和平交接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在文化和历史上的特殊联系。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国家身份要有同质性,信奉和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这样就容易建立信任和协调利益关系。1947年英国对希腊的支持维持不下去了,就自然地把接力棒交给了美国。在美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英美特殊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是超脱的国际政治环境。美国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处在国际政治的中心,也不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因此不受当时大国纵横捭阖的政治纷争的影响,可以专注于自身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初就有可能介入到列强的角逐中去,但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如果美国快速崛起,又不断插手欧洲事务,那么它的国际政治环境就会复杂化。
第五是有机可乘的软实力环境。美国开始崛起的时候,其他的大国已经提不出新的国际政治理念,他们信奉和实行的都是老一套的大国均势、结盟、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等,两次世界大战表明传统的国际政治走入了死胡同,迫切需要新的理念来指导国际关系。美国提出的一些核心理念,如非殖民化、民族自治、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等,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和时代性,到了二战以后大行其道。二战之后唯一能够提出另一套不同理念的是苏联,但苏联提出的那套理念对以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现代民主制度为立国之本的国家水土不服。
最后是几乎空白的国际制度环境。在二次大战之前,谈不上有真正的国际合作与治理机制,这种几乎空白的国际制度环境为美国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历史机遇。美国的崛起和霸权地位的确立最终表现在制度霸权的建立,二战以后美国一手主持建立了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等。由于当时国际机制处于一个空白状态,所以美国创制要相对容易一些,如果已经有了一套国际机制,那么对其进行改革难度会更大。
以上是美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中的静态因素。外部环境中还有动态因素,那就是历史机遇。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没有这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突破不了国内孤立主义的羁绊,没有机会将其国际治理理念付诸实施,也不大有机会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显然,美国崛起的外部环境的静态因素很独特。从借鉴的角度思考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要考虑到第一,美国外部环境中哪些因素我们现在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第二,哪些因素我们现在没有,但是可以从无到有,积极塑造;第三,哪些因素,我们现在有一定的基础,今后可以充分放大。至于美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中的动态因素,即两次大战提供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有新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核武器的存在、经济相互依存等),历史机遇的表现不再是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大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危机,危机会引起大国之间力量的调整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包括话语权和领导权的转移。因此我们要注意研究下一场危机可能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危机,何时以及可能在何地发生,这场危机有可能带给中国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