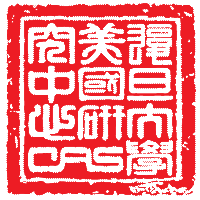近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持续进行着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起,美国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主要由安全上的战略克制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构成——是否失败了?可以说,这场辩论不仅是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内容最深刻、受关注度最高的一次。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连同各自的战略选择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与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减,使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出现了“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从2009年奥巴马执政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始,在美国致力于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中国对外战略却逐步完成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型。可以说,实力对比与战略选择同时变化所引发的“共振”,加剧了美国战略界的焦虑。
这种焦虑自2017年底以来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接连出台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报告和法案、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以及整个西方战略界掀起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对华战略似乎正在告别过去四十余年的既有框架,在安全上转向战略制衡,经济上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开始担忧中美陷入“新冷战”的风险。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尽管美国的战略精英似乎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但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当前美国对华战略正在进行的调整,以及如何研判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笔者的答案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成功的,只不过当前美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及其排序出现了问题。
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全与经济两个核心维度构成的。就安全而言,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和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ing)是两种基本形态;就经济而言,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和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成为两类政策取向。因此从理论上讲,安全与经济的不同组合塑造出遏制(战略制衡+经济民族主义)、对冲(战略制衡+经济自由主义)、接触(战略克制+经济自由主义)及挂钩/克制(战略克制+经济民族主义)等几种不同的战略形态。按照这一分析框架,1949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首先,从1949年到1971年,美国的对华战略表现为遏制。其次,从1972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特征为接触。最后,自2009年起,美国的对华战略开始进入中长期意义上的调整和过渡阶段,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这就导致其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例如,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将其对华战略逐步转向对冲,但特朗普执政后,由于国内政治出现的新变化,美国的对华战略又呈现出朝着挂钩/克制方向演化的趋势;近期的一系列态势则表明,在美国国内“建制派—全球主义”力量的影响和干预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存在转向遏制的风险。
为何美国的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为何当前美国的对华战略进入到了调整和过渡期?本质上,这一问题取决于美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及其相应战略选择。自二战后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以来,维护自身全球地位始终是美国最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利益。在这一总体利益之下,安全、经济、价值观及国际秩序的稳定是美国更为具体的核心利益,并且在不同时期,这些具体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又因其对维护美国总体利益的不同价值,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取向。
在冷战时期,安全是美国的首要核心利益。因此,美国的对外战略就在于遏制苏联扩张带来的安全挑战。为此,美国在对华战略上先是对作为苏联阵营主要成员的中国进行遏制,后又基于美苏、中苏战略态势的变化务实地调整了对华战略,从遏制转向接触,其最终目标始终是应对苏联构成的安全威胁,维护其全球地位。从实践及其结果看,冷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安全上成为牵制苏联扩张、最终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最重要地缘战略因素。
冷战结束后,经济取代了安全的首要地位,尽管“9·11”事件使安全的重要性有所回升,但已无法与冷战时期相提并论。因此,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致力于运用自身优势,通过引领经济全球化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例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三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经济始终是最重要的议题。基于此,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接触战略主要出于中美经济互补性极强的现实,以及通过接纳中国成为其主导的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增强自身国际领导力和秩序稳定性,最终维护其“一超”地位。从实践及其结果看,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也是成功的:美国从中美关系中得到了切实经济利益,这对于其收获冷战后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进而稳固其全球地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出现的深刻变化,使美国很难再像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初期那样对核心利益进行明确排序。虽然维护自身“一超”地位这一总体利益没有变化,但经济、安全与国际秩序稳定等具体利益如何定位,是美国面临的战略难题之一。这就导致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了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初期两个阶段所拥有的明确和稳定的战略基础(遏制苏联与发展经济),陷入一种漂移状态。例如,中国在经济、安全与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稳定等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上,都与美国形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结果是,美国对于上述核心利益排序的变化及其反映出的差异化对华战略诉求,引发了全然不同的对华战略结果。在奥巴马时期,安全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首要考虑因素。尽管美国在此期间致力于延续冷战结束之后的对华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同中国开展合作,从而在推进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增强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然而作为其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亚太再平衡”意味着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和挑战者,致力于在安全上进行对华战略制衡,最终牵制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后,随着经济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首要利益诉求,美国的对华战略开始由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目标是大幅减少贸易逆差。同时,为了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在安全上对华推行战略克制,运用挂钩的方式同中国进行利益交换。这一转向使得美国的对华战略与奥巴马时期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并且在2017年的中美战略互动中大体得以顺利运转。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内将安全视为对华战略首要方向的政治力量,自2017年底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行政、立法和智库等渠道大规模作用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这就表明,美国对其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和排序延续了2008年以来的模糊特征,并且由于国内政治极化和分裂的加剧而显得更为混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问题,那也绝非接触战略所致,而是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所自我界定的利益及其排序出了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国内政治的极化和分裂起到了明显的负面作用。事实证明,接触战略是成功的,美国国内战略共识的缺乏及其引发的战略漂移才是危险的。在对华接触战略推行的时期,美国因自身核心利益排序变化而引发了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变更,经历了从安全到经济的演化。在这一转换期,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经历了短暂的漂移。基于历史经验,美国的对华战略应尽快走出这种漂移,在新的背景下寻求双边关系发展的战略基础。(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本文首发于“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