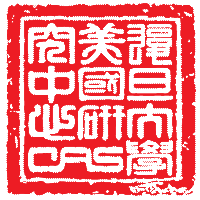进入后冷战时代后,人们一度产生幻觉,以为没有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与军事集团对抗的世界,必然是更美好的时代。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国应该更好发挥稳定世界的积极作用,给人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具体讲来,后冷战时代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缺少国际制约的情况下,理应更有成效地为维护国际法制、增进人类福祉做出贡献。同时,那些新兴经济体也应为维护国际法制提供更多资源,人类因而更有希望见到各国长期孜孜以求的和平与发展。
确实,在后冷战时期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也曾努力过。克林顿政府积极推动世界自由贸易,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入世的关键阶段。克林顿政府还推动世界就全球减排温室气体达成《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政府推动全球反恐,为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做出努力。奥巴马政府则在反恐框架下,促进了四届核安全峰会的举行,并为世界达成《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做出了有益贡献。
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曾大力推进多边国际合作,在自身做出合作承诺的同时,推动就全球治理达成国际共识。这种跨国界的国际合作,范围从朝核到伊核,从反恐到气变,从阻隔传染病传播到稳定国际金融,几乎无所不包。由于美国的倡议在兼顾私利的同时,也往往兼具某种公益性,各国多少还是接受了华盛顿的一些主张。
但同时,历届美国政策也政出多门,政策往往前后抵消,目前的发展则是日趋消极。譬如,克林顿政府促成《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政府时就予以退出。奥巴马政府推动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则退出该协定。就朝核问题,克林顿政府采取接触政策,小布什政府则同朝鲜敌对,称对手为“邪恶轴心”,而奥巴马则采取毫无作为的“战略忍耐”态度。当特朗普政府上台,白宫则高燃针对朝鲜的“烈火与怒火”,号称对朝鲜的一切政策选择都在桌上,明显威胁朝方。
特朗普政府执政才两年,美国对外政策已经出现全面倒退,这已严重影响在许多重大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国际合作。这期间,美国不仅退出《巴黎协定》,还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框架下的伊核协定以及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合作平台。这些协议曾是美国竭力打造的国际合作框架,它们不仅服务于美国利益,也是稳定世界安全和促进人类发展的国际公用品。但在今日美国,只要“美国第一”,哪顾共同发展?在当今白宫眼中,为了“美国优先”,美国可以放弃世界。
美国日趋单边主义,自私自利,已经放弃引领世界并通过合作来推进共同发展和安全的道德高地。那么,世界呼唤其他大国勇于担当,发挥国际合作的引领作用,从而给世界提供新动力,凝聚新共识,也就十分自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融入世界并共同建设世界的国际合作道路上取得重大进步。在促进国际自由贸易问题上,中国入世时做出积极承诺并一直在积极践行。在国际反恐问题上,我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展合作,并在联合国框架下,从边防到金融都采取了积极进取的协助措施。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以及叙利亚化武等问题上,都采取了塑造合作的积极姿态。我国促成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尊重朝鲜正当安全的同时,推动朝鲜弃核与国际社会相应地分阶段解除制裁的“双轮驱动”,并为推动美朝直接会谈创造条件。关于伊核问题,中方不仅主张尊重伊朗发展民用核能的正当权利,而且与各国一起安排伊朗对其核能计划做出必要限制,我国还提出为伊朗改建重水反应堆提供方案和技术,有力促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达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不仅更加积极投入到关于气变和阻止各种传染病传播的国际合作,而且在推动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做出顶层设计,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赢得世界各国普遍欢迎。这项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超级国际合作,力图提高欧亚大陆陆路、海路以及空路等方面的联通能力,并进一步将此延伸到关于能源、通讯等全方位的基础设施方面,其规模和内涵为人类此前所未有。中国为此设定“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在实施了第一阶段后进一步提出建设高质量的“一带一路”。我国引领创建了与此相关的亚投行,并在最短时间内按国际通用标准打造了一个高质量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
中国从与国际社会合作而受益,到为国际合作不断做出贡献而获得接受,期间发展速度十分可观。我国以自己的合作理念和不断增长的国力来提升新世纪的全球治理水平,已经占住了相当程度的国际道义制高点。中国当前奉行的国际合作,采取的是有给有得的双向互惠模式,因此具有更牢固的可持续性。这种模式,既不是那种纯粹给予的“奉献性”国际援助,更非目前有的国家罔顾国际利益的自私性方式,因此具有不仅能占住、而且能占牢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坚实基础。
我国已崛起为国际社会的新支柱国家之一。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化,中国与各国团结合作的灵魂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这在根本上有利于本国与世界。显然,中国走到世界道义中心,成为引领性国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国际特征。(作者沈丁立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文章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