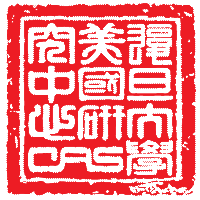进入2月以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选战正式打响。经过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四州初选的激烈竞争,候选人即将迎来更具挑战也更为关键的3月3日“超级星期二”,届时包括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人口大州以及阿拉巴马、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等南方州在内的16场初选将举行。这些州的初选代表票累计达1357张,超过民主党全国代表总票数(除771张“超级代表票”外)的三分之一。因此,“超级星期二”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主党初选的结局。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对民主党初选选情进行一下梳理,会发现一些颇为有趣更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一、2020民主党初选与2016共和党初选相似度很高
纵观2020年民主党初选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2016年共和党初选。从参选人数看,两次初选都创下1972年现行初选制度以来的纪录:2016年共和党有17人参加初选,超过1976年民主党初选16人的纪录;而2020年民主党初选的参选者更是超过20人。创纪录的参选人数表明,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程度和“否决政治”的发展已趋于极端,两党对对方执政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而就竞选态势而言,两次初选初期(即“超级星期二”之前)都给人以党内不同派别“混战”的感觉,其中属于非主流和反建制类型的候选人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初期,党内存在温和派、保守派和反建制派,而反建制的“三无”候选人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莱纳大获全胜,仅在艾奥瓦输给了克鲁兹,进而为其在“超级星期二”领先优势的扩大(12个州中拿下7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初期,党内则存在温和派和激进派,其中激进派代表、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不仅取得艾奥瓦和内华达州的胜利,而且在全国民调中大幅反超了前副总统和作为温和派代表的拜登,展现出异常强劲的竞选势头。
可以说,同样作为体现国内不满情绪及改革呼声的非主流和反建制派,同样得益于日益严重的两党极化和党内分化局面,同样在初选初期气势如虹,2020年的桑德斯看起来很有希望成为2016年特朗普的翻版,进而锁定党内名额。然而事实上,桑德斯的进阶之路相比于2016年的特朗普或许变数更多、不确定性更大。
二、2020桑德斯能否成为2016特朗普翻版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从候选人自身状况看,桑德斯能否在后续初选中取得与2016年的特朗普相当的战绩仍存不确定性。在2月份举行初选的四州中,桑德斯在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的不俗表现源自上述两州选民主体是白人,而他在内华达州的领先优势则在于拉美裔选民是投票的中坚力量。这一特点反映出桑德斯在医保、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更能吸引自由主义者和拉美裔。然而,在刚刚结束初选的南卡罗来纳的选民结构与前三个州不同,大约60%为非洲裔选民,所以拜登的表现更为抢眼。这就表明,在黑人关心的经济和就业问题上,桑德斯存在一定劣势。基于此,桑德斯在“超级星期二”中赢得阿拉巴马、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等黑人选民聚集的南方地区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对桑德斯而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在代表票加起来超过600张的两个人口大州——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目前其相对于其他候选人的民调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加州,桑德斯的民调支持率达35%(沃伦14%、拜登13%、布蒂吉格12%),较12月时上升15个百分点,拜登则下跌8个百分点。在德州,桑德斯、拜登、布蒂吉格和沃伦的支持率则依次为29%、20%、18%、15%。
第二,从主要竞争对手看,桑德斯当前面临的党内压力大于2016年的特朗普。2016年共和党初选时特朗普异军突起的原因,除天时地利外,人和也是一个因素。例如,初选前被主流媒体看好的杰布·布什,在选举初期的表现即让人大失所望,早早退出宣战。有人将2020年的拜登类比为2016年的布什,认为同样作为建制派和温和派,拜登会像布什一样不合时宜。但尽管拜登在前三场初选中表现低于预期,南卡一战则表明他并非平庸之辈,而是有可能借势而起,在“超级星期二”取得良好战绩。一旦拜登能够达到使桑德斯的初选全国代表票低于总数的一半即1991票,他就有可能在第二轮超级代表参与的投票中逆转翻盘。因此,拜登仍是桑德斯进阶之路上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从两党初选制度来看,共和党初选制度更有利于非主流和反建制候选人胜出。首先,共和党基层初选大多采用类似于大选的“胜者全得制”,某一州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将拿到该州的全部代表票。其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不存在类似民主党的“未承诺代表”或“超级代表”,基本上按照各州初选结果产生本党候选人,因而党内精英对选举结果的控制程度更弱。这意味着各州初选获得优势的共和党候选人将几无悬念地锁定党内提名。然而,民主党初选制度则与之大不相同。首先,各州初选采用的是“比例代表制”而非“胜者全得制”,参选人按照得票比例分配该州代表票,从而削弱了优胜者的领先优势。其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时存在771张“超级代表票”,按照2020年选举改革的规定,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未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承诺代表票”即各州基层初选票,那么超级代表将在第二轮参与投票,最终决出获胜者。不难看出,民主党的初选制大幅增加了候选人在首轮出线的难度,因为“比例代表制”使各州初选产生的“承诺代表”票被大幅稀释,很难有候选人在第一轮即获得半数(即1991张)选票。进入第二轮,以党内主流精英为主体的“超级代表”就有了相当大的左右最终提名人选的运作空间。知名选举预测网站FiveThirtyEight的最新分析认为,桑德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投票首轮胜出的概率仅为29%,有51%即超过一半的概率是无人在首轮投票中能够获胜。假若如此,候选人的最终命运仍将交由771位“超级代表”决定。显然,这一事实对桑德斯不利而对拜登有利。
不过,基于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我们也不能完全参照历史案例判断。一方面,对民主党而言,2020压倒一切的核心在于“谁更有机会击败特朗普”。基于2016年的经验教训,拜登在出战特朗普时能比希拉里拥有更大胜算吗?这是一个党内精英的重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桑德斯延续甚至扩大目前的领先优势,民主党内精英是违背民意进行投票、还是顺应民意并基于两党竞争态势做出选择,同样存在变数。总之,2020桑德斯究竟是不是2016特朗普的翻版,以及拜登会不会变成“白等”,目前看依然无法做出判断。
三、两党选举困境反映出美国政治已从对等极化演化为断层极化
2020年民主党面临的上述选举困境与2016年的共和党如出一辙,其背后的根源在于,近年来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发展,已经从两党势均力敌的对等极化进一步恶化为断层极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开启并于冷战后逐步深化的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缓慢冲击和重塑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那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使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包括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在美国全方位突显出来。这一趋势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在政治上推动民主、共和两党及其代表的国内政治联盟的立场更趋极端。结果是,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的特朗普现象,以及与之同时出现并可能深刻影响民主党2020年大选进程的桑德斯现象,标志着美国政党政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三大“断层线”。
一是政治联盟断层线。一方面,两党联盟内部多元性进一步消失、一致性进一步增强:随着白人蓝领阶层倒向共和党,民主党政治联盟的主体构成越来越朝着少数族裔方向发展,共和党则日益成为一个白人的政党。另一方面,两大联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增大,在涉及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议题领域,美国政治的极化程度都在加剧,而且除传统的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外,移民问题、族群矛盾以及政治正确等成为全球化负面效应持续显现背景下美国政治新的博弈焦点和冲突来源。
二是意识形态断层线。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党重组导致的对等极化,使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断加深,进而表现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分别主导了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进程。随着2016年大选后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的出现尤其是国内政治联盟断层线的形成,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化达到新的高度。一方面,民主党内激进派—进步主义者影响与日俱增、传统温和派力量弱化,使民主党作为整体进一步“左”转。另一方面,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崛起,则成为该党不断“右”转的信号。这一点在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构成及其就任以来推行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中已经被充分体现。同样重要的是,近年来两党意识形态断层线的形成,除受到传统的左、右之争加剧推动外,还在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冲击,为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注入了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两大相互对立的观念元素,从而使之变得更为复杂。
三是文化—价值观断层线。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一直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文化(即“瓦斯普”或WASP文化)。著名的“熔炉论”就认为,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后会被这一主流文化—价值观同化,由此成为美国“合众为一”的重要注脚。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当代美国政党政治对等极化格局下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显著优势,“瓦斯普”文化的核心地位受到冲击,并且其程度随着美国人口结构不利于白人的变化趋势日益加深。结果是,近年来美国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使得以白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迅速崛起,其中史蒂夫·班农代表的另类右翼群体在文化—价值观领域主动向多元文化主义发起了“反击”。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白人认同”正在受到运用“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来削弱白人和“白人文明”的多元文化力量的攻击。这就意味着,当代美国的“文化战争”在特朗普执政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围绕“我们是谁(who are we)”的争论和博弈上升到关于“谁是美国人(who are Americans)”、“美国是谁的美国(to whom America belongs to)”的抗争,由此加深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裂痕。(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
专题:2020美国大选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