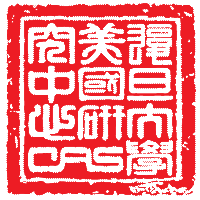拜登政府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纪录,他的核心团队跨越整整四代。其中,“寂静一代”(1928-1945)有两人,分别是出生于1942年的拜登自己,以及出生于1943年的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婴儿潮一代”(1946-1964)仍是拜登团队的核心,共有15名内阁成员和内阁级官员,包括1946年出生的财长耶伦、1962年出生的国务卿布林肯等。“X一代”(1965-1995)共11人,包括1974年出生的贸易代表戴琦、1976年出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们已经体现出从“婴儿潮一代”手中接班的明显趋势。“千禧一代”(1996年以后)首次进入内阁,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出生于1982年。
美国代际政治的转变在社会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传统上,美国代际政治现象并不明显。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差异,主要与族群、社会阶层和个人阅历等因素相关。年轻人虽然有叛逆的天性,但美国政治结构和选举设计又压制了年轻人的政治道路,导致美国年轻选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不大。年轻人的叛逆本能很难形成一致性的政治颠覆力量。等到年轻人积极性上升的时候,在政治上又往往成熟了。哪怕是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进步运动和反战运动浪潮中,年轻人也主要以社会文化运动的形式表达出来,很少组织起来去直接影响选举结果和决策过程。美国决定退出越南战争,主要是国际政治格局演变对美国不利和经济困难所致,反战运动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并不是主要因素。
但最近几年,尤其2020年总统大选过程中,美国政治出现一些重大变化。
一是长期消极的年轻选民突然被动员起来,并成为决定性政治力量。年轻选民突然对民主党压倒性支持以及突然上升的政治积极性和投票率,导致美国投票结构剧变,是导致拜登胜选的主要原因。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美国选民,2/3选票投给了拜登。
二是年轻选民的多元与分化现象非常严重。在这次总统大选中,18-29岁的白人选民中有44%支持拜登,有53%支持特朗普。而在同年龄段的黑人选民中,支持拜登的占89%,支持特朗普的只有10%;在拉丁裔选民中,这一比例则是69%和28%。在20年前小布什对戈尔的总统大选中,这一年龄段选民对两人的支持率是一比一平。这说明今天的美国年轻人在政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加多元、对立,认同政治属性明显高于民主政治属性。而且美国年轻一代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政治立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政治钟摆效应和自我平衡机制面临新挑战。“千禧一代”的很多人已30多岁,但总体支持民主党的态势未变;即使有所变化,也只是从极端的民主党人变成温和民主党人,变到共和党一边的可能性很小。
三是美国选民结构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根据2018年一项统计,“寂静一代”占当时美国成年人的11%,其中白人占79%;“婴儿潮一代”占成年人口的29%,其中白人占72%;“X一代”占成年人的26%,其中白人占61%;“千禧一代”占成年人的28%,其中白人占56%;“Z世代”占成年人的5%,其中白人占53%。“Z世代”是美国历史上族群结构最多元的一代。2019年“Z世代”中白人占52%,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在2020年一份统计中,18周岁以下美国民众之中,有50%属于少数族裔。在美国不同世代的选民中,白人的主导地位一直被削弱,多元化趋势非常清晰。
种族结构的多元化、信息来源的网络化以及随着美国霸权收益逐渐减少而对国内收入结构的冲击,导致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政治上更加早熟,也更分裂。这使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有可能被大众民主或民粹政治的新形态进一步替代。这个年轻的选民群体在新一代政治家引领下,正在推动美国朝着非常规的方向发展。
在国内,美国年轻选民希望看到一个更大的政府,以解决医疗保险、学生债务、毒品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越年长的美国人越倾向于小政府,而越年轻的美国人,则越倾向于扩大政府职能。2020年美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年长的人对特朗普总统的不满意度要明显低于年轻一代。这些年长者虽然更容易受到疫情伤害,但他们对大政府的担忧可能还在疫情之上。同时,在民主党的不同世代之间,对种族、性别和政府功能等重大议题的态度比较接近。在共和党人内部,不同世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则差异较大。例如,在共和党人中,52%的“Z世代”支持一个更大的政府以解决问题。这一比例在“千禧一代”中为38%,在“X世代”中为29%。在民主党人,支持更大政府功能的在“Z世代”中为81%,在“千禧一代”中为79%,在“X世代”中为70%,相差不大。这说明,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正沿着符合民主党价值观的方向在发展,并对共和党起到撕裂甚至重塑作用。
美国年轻选民在美国国际地位的态度却可能是相反的,仿佛并不热衷一个“大美国”的出现。这些年轻选民对国际议题、宏大叙事兴趣不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气候变化、民主、人权、少数族群权益等议题,更加注重与各方的协调与合作。
总体来看,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更加均衡多样,美国也将逐渐常规化、普通化。这不仅将意味着美国的时代性调整,可能也是世界政治再平衡的一个重大契机。(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