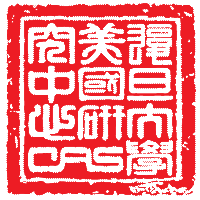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来源:中美聚焦,2024-03-04)
地缘技术(geo-technology)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审视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博弈提供了新的视角。美国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紧迫感日益增强,沙利文称美国仅保持领先是不够的,需要尽可能拉大与对手之间的技术差距。这预示美国将为中国的研发活动制造更多阻力,甚至会设法“推回”中国业已取得的技术进步。
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命题。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深入互动使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成为重要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并推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国际经贸机制之间的制衡、“友岸外包”和供应链重塑等问题,对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越发明显。
正如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等人所言,美苏主要通过军事力量进行冷战,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新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则是由技术领导力所决定的经济实力竞争。

▲美国MSNBC3月1日发布的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采访中,雷蒙多对中国汽车发表惊人言论,宣称,“假如有300万辆中国汽车行驶在美国道路上,而北京可以让它们同时熄火。”
地缘技术(geo-technology)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审视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博弈提供了新的视角。拜登政府多次表示,技术竞争是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中国凭借其技术实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和竞争的时代,美国必须确保自身处于全球创新的前沿。
概言之,地缘技术主要包括三方面意涵。
第一,技术水平是影响不同国家力量对比的关键变量,技术因素在一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技术水平的高下对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也是与发展模式、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的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从世界历史的长视角看,技术进步为大国崛起、军事和战争模式变革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进而深刻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大国竞争也常常是重大技术变迁的催化剂。

▲OpenAI视频模型Sora生成的画面
当今时代,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在此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技术因素对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大国围绕“创新力”(innovation power)的竞争越发激烈。基于应对大国竞争的考量,很多国家设法减少在技术方面对竞争对手的依赖。为了增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技术因素的把控力,拜登政府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增设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位,并在国务院设立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旨在回应技术因素在大国竞争中不断提升的重要性。
第二,高技术企业等行为体对大国战略博弈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深度融合在大国技术竞争中更为突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拔尖的跨国企业拥有“超级权力”,深刻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认为,技术企业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玩家”,与传统国际政治的单极、两极或多极体系相比,“技术极”(technopolar)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技术企业可以“决定国家如何投射经济和军事力量、塑造未来的就业并重新界定社会契约”,构建大国博弈所依赖的全球环境。
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言,谷歌、英特尔、特斯拉等高技术企业以及相关的科技和产业协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通过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理事会、国会创设的“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制,技术专家和高技术企业负责人为美国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政策建言和实际支持。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提供的“星链”服务、星球实验室公司(Planet Labs)提供的卫星图像情报等成为影响乌克兰战事的关键因素,这些高技术企业推动世界军事进入智能化作战的新时期。

为确保长期占据超强技术优势,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增加政府对研发活动和高技术产业的投入,推动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重塑,加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协作,大力打造针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
第三,与技术因素高度相关的联盟或阵营构建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技术之争与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竞争紧密联结。为强化针对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注重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技术联盟,力图加大情报共享,并在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增进政策协调,以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目标。这类技术联盟还具有推动联合融资、共同研发的功能,其目标是提供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选择”,削弱竞争对手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此外,技术联盟注重应对国际技术标准、新兴技术治理、科研伦理等方面的大国竞争,如增强西方国家对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组织的控制力,确保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符合所谓民主价值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下,技术之争越发呈现“跨域竞争”的特征,即供应链、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因素与技术竞争深度捆绑,如拜登政府在“民主峰会”框架下设立的“出口管制和人权倡议”。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地缘政治机制,也越来越多地被嵌入技术竞争的功能。美国试图将技术因素尤其是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新兴技术作为地缘政治阵营构建的粘合剂,以应对“数字威权主义”“经济胁迫”“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等为驱动力,打造所谓“民主技术联盟”。
近年来,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全力实施竞争性对华战略,宣扬美中较量迎来“决定性十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前助理国务卿帮办、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战略界人士认为,技术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挑战结合在一起,已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焦点。
美国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紧迫感日益增强,正如拜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所言,美国仅保持领先是不够的,需要尽可能拉大与对手之间的技术差距。这一讲话体现了美国对华技术竞争战略思维的重要转变,预示美方将为中国的研发活动制造更多阻力,甚至会设法“推回”中国业已取得的技术进步。无疑,中国需准备迎接来自美国的更大力度的技术施压,尽力确保自身发展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