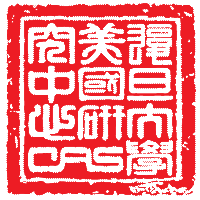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盟体系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支轴”,不仅确保了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军事力量投射,还为美国增强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施展国际领导力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撑。正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美苏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苏联这样一个重大的“共同威胁”,美国的联盟体系出现松动和“漂流”的迹象,美国与盟友之间在安全成本分担等问题上龃龉不断,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加剧了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的摩擦和分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了快速崛起,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不断深化,其联盟构建的基点也开始逐步向中国偏移。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利·韦恩(Ali Wyne)认为,20世纪美国面对日本、纳粹德国和苏联三大“无处不在的挑战者”,并在与它们的争斗中获胜。冷战的结束让美国陷入一种“战略失向”的困境;中国的崛起实际上“给予美国一个宝贵的机会,使其重回熟悉的取向——对抗无处不在的挑战者”。
从历史的长视角看,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常会引发美国结盟行动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受到对手特性的重要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中国被视为不同于苏联等过往对手的所谓“特殊挑战”。中国与美国的大多数盟友和伙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国在经贸、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拥有综合性实力,中国还深度融入了既有的国际体系。拜登本人曾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中国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挑战……中国正在推进长期博弈,包括扩展其全球影响、推广其政治模式、投入研发主导未来的技术”,“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强硬……应对这一挑战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建立美国盟友和伙伴构成的统一阵线”。
美国在亚太构建“小多边”联盟
第一,全面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拜登政府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视为推进“印太战略”的核心平台,并将其升格为元首和首脑级别的机制,已举办多次峰会。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围绕海上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议题设立专门工作组,各方在部长级和司局级层面展开频繁磋商。
尤其是,美日印澳四国自诩“海洋民主国家”,大力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近年来,四国多次在孟加拉湾、菲律宾海等区域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派出航空母舰、直升机母舰等大型舰艇参演。四国还推动实施“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IPMDA)计划,力图在东南亚、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等多个区域提升海上安全情报搜集能力,深化海警和海上执法合作。上述举措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味。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力图扩大合作对象,进一步织密制衡中国的地区性网络,一是将韩国、越南作为重点拉拢对象,推动这类“中等强国”对华加大战略牵制;二是有意吸纳作为“五眼联盟”成员的加拿大、新西兰;三是重视与东盟之间的互动,拜登政府在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对此加以强调。
另一个四边机制,即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合作(I2U2)值得关注,它未来或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动。2021年10月18日,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召开外长会议,议题包括政治合作、经贸关系以及海上安全等,标志着该机制正式成立。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战略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卡比尔·塔内贾(Kabir Taneja)称,西亚四边机制的出现,表明印美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东西两个四边机制可以相互加强,从而全面制衡中国的影响力。
第二,加紧充实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带有“进攻性”色彩的联盟机制,也是拜登政府对华实施“一体化威慑”的重要平台。该机制旨在围绕对华战略竞争打造“盟中之盟”,美国力图使这一“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具有高水平的信任度、协同性和行动力,它被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称为“最重要的战略创新”。
为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目标,美国试图借此增强盟友的远洋作战能力,建立跨越多岛链的对华威慑网络,协助美军在战时封锁主要海上通道。三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包括美英澳签署《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耗资100亿澳元在澳东部海岸新建潜艇基地、美澳围绕核动力潜艇加大联合演训。三国已正式确定建造核动力潜艇的具体计划。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注重加强在前沿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方面的协作,体现了美国“防务能力外包”的政策态势。该机制聚焦的前沿军事科技主要包括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电子战、网络战、人工智能与自主性、量子技术以及海底能力。美英澳三国的军工复合体也在深化合作,力图增进防务供应链和“防务工业基础”(Defense Industrial Bases)的一体化程度,共同研发和生产军事装备、弹药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西兰、韩国、印度等国希望参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的相关合作。该机制与其他亚太“小多边”机制之间的联动也将增多,包括五国联防(FPAD)、澳新美同盟(ANZUS)等,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盟伴体系中“穿针引线”的作用更为凸显。
第三,不断深化美日韩、美日澳等三边协作。
拜登政府将推动美日韩三边关系作为“印太战略”的主要着力点。在拜登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是其列出的10项行动计划之一。
近年来,美日韩多次举行三边峰会,并推进外交、国家安全、军事、情报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边磋商。拜登政府加大对韩国尹锡悦政府拉拢,力促日韩缓和紧张关系,美日韩三边军事演习也在中断多年后得以重启,涉及反潜、反导、两栖作战等实战性科目。该机制看似剑指朝鲜“核导威胁”,但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也越发突出。
未来,美国或通过加大美日韩三边互动,优先实现三方军事情报共享,将其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与在日本部署的海基“宙斯盾”系统、陆基“爱国者”系统加以整合,构建美国主导的区域反导体系。美日韩正规划在今年8月底于华盛顿举行三国领导人峰会。
美日澳三边关系也在实质性增强,美国试图使其亚太盟伴体系的“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紧密相连。近年来,在美国大力支持下,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关系显著强化,两国首脑发布新的《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双方多次举行外长和防长参加的“2+2”磋商,并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等军事协议。
2022年10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防长举行会议,对中国妄加指责,提出要大幅加强美日澳三边防务关系。美澳还邀请日本在澳派驻军事力量,日本还考虑将从美国购置的F-35战机等先进武器部署在澳大利亚。美日澳在网络战、太空安全等领域的协作也在不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希借美日澳三边关系推进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布局,如美日澳联手提升菲律宾的安全能力、通过美日澳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在太平洋岛国削弱中国影响力。
美国亚太“小多边”的对华影响
在美国方面持续推进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背景下,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和周边外交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其一,美国亚太“小多边”机制恐削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信任,增大中国参与和引导地区事务的政治成本。
美国力图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孤立,给中国贴上地区秩序“破坏者”、地区安全“威胁者”标签,以“捆绑中俄”的策略抬升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认知。2022年6月,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诬称,“印太国家不应面对政治恫吓、经济胁迫或军事骚扰。中国的动作,是要威胁破坏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及繁荣。”
美国利用亚太“小多边”机制塑造和固化盟伴对中国的认知,通过发布联合声明等方式,在国际舆论中散布涉及中国的负面论调。借助各类“小多边”机制,美国将钓鱼岛、南海、台海、中印边界等问题相互缠绕,在亚太地区盟伴中不断凝聚“对抗中国”的共识,
应该警惕的是,美国在亚太“小多边”机制中更加注重应对非法捕捞等“民事安全挑战”,力图借助这类“软安全”议题对中国实施“硬遏制”,增加中国的“声誉和形象成本”,给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推进地区合作制造更多阻力。
随着美日印澳、美日澳、美日印等“小多边”机制不断发展充实,亚太地区一些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或会上升,将对中国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带来冲击。
其二,美国亚太“小多边”机制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增强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军事安全压力。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统计,2021年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军事支出为5869亿美元,上涨3.5%,超过欧洲的4180亿美元支出和3%的增幅。美日澳等亚太“小多边”机制以军事安全合作为重点,亚太地区国家的军备建设将难以避免地受到其刺激,也会对地区国家管控军事冲突、防范安全危机升级等带来新的考验。
美国在操弄“中国威胁”基础上,通过美日澳、美日韩等机制,不断强化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相关“小多边”机制的对华战略指向性更加显著,进攻性、实战性趋强。特别是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化,将改变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新的威胁。
美国以“太平洋威慑倡议”等计划为抓手,将双边运作与“小多边”相互结合,推动盟友提升针对中国的“拒止性威慑”能力,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盟伴更加注重强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作战能力、推进各军兵种联合多域作战、加强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等。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等在情报共享、作战规划和协同行动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这有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塑造攻防兼备、灵活韧性的军力部署态势,形成盟伴协同的作战效能,给中国带来更大军事压力。
其三,美国亚太“小多边”机制对中国在该地区产供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或会带来一定程度冲击。
这类“小多边”机制是一种复合阵营,美国力图整合政府和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之间的力量,以“官民”一体方式对中国施压,尤其是在美国对华经贸和科技竞争方面。
美国利用美日印澳、美日澳、美日韩框架下的经济安全政策协调机制,并借助“印太经济框架”(IPEF),拉拢地区国家对华进行“协同脱钩”,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消解中国与美国盟伴之间的经济联系。拜登政府注重与盟伴共同构建“多元、开放和有预测性的”供应链,尤其是在芯片、关键原材料和矿产、药品等领域。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国推进实施“供应链韧性倡议”,旨在策应美国“友岸外包”策略,减少对华经济依赖。
美国亚太“小多边”机制聚焦数字经济、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展等议题,强调要推动“负责任的互联互通”,支持符合透明、法治、环保等原则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美日澳借助所谓商业腐败、劳工权利、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合作进行制衡,强化对华地缘经济竞争。
在拜登政府希望打造的“民主科技联盟”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亚太地区国家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澳三边关系等框架下深化盟伴科技合作,致力于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方面扩大对华领先优势,通过实施“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人才奖学金”等项目构建盟伴创新生态,挤压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科技合作空间。
随着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其更加注重“拉帮结伙”,对华施压的阵营性特征越发突出。事实上,自上台之初,拜登政府便力图在亚太地区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注重借助多样、灵活的“小多边”机制,促进美国的条约盟国(即与美国签署正式盟约的国家)与新的安全伙伴之间力量的深度融合,谋取对华“实力地位”。毕竟,在地缘政治中,没有比联盟更划算的买卖了。
赵明昊,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