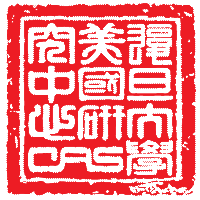王浩:《从马斯克组党看美国政党政治流变》,《世界知识》,2025年第15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近来围绕“大而美”法案产生的深刻理念分歧与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引发严重政治分裂,致使两人从此前亲密无间的战友转变为相互敌视的对头。在“大而美”法案经国会两院投票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生效后,马斯克立即宣布成立“美国党”,誓言以之代表“两党夹缝中的80%中间选民”,让人民“有发言权”。从具体政治目标来看,“美国党”力图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搅局者”,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瞄准2~3个和8~10个议席,以图终结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微弱多数地位,并为受困于共和、民主两党之争而无法推进的重大议程提供关键杠杆。作为美国政治中组建第三党的最新尝试,“美国党”与历史上的先例有何异同,又将对美国政党政治走向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结合美国政党政治的流变进行分析。
美国两党制成因和第三党的微妙作用
尽管美国立国之初的制宪者们对党派政治深恶痛绝,美国宪法中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政党,但现代政党还是在美国应运而生。对此,多元主义流派、社会分层学说和民主化理论等从不同角度纷纷论证了政党出现的必然性。美国历史上,最早的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这两大特色鲜明的政党在华盛顿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便开始形成,由此奠定了美国两党制的基础。此后,经过一系列政治实践的演化,民主党与共和党成为美国两党制的主体。从1860年开始至今,在历次美国大选中脱颖而出的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
美国政党政治史上并不缺少第三党,比如曾经的美国独立党和国家进步党,即便今天也仍有自由党、宪法党、绿党等小党存在,但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两党制得以持续稳定地运行。为何如此?既有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首先是制度理论,即美国以单名选区(又被称作“胜者全得”)为核心特征的选举制度,使得每个选区只能是得到相对多数票的一名候选人被选为代表,其他所有候选人无论得票多少都无法出线。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赢得选举的需要会推动不同政治力量进行整合壮大,最终形成两个主要政党彼此博弈的格局,第三党始终面临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压制。第三党还面临极高的参选门槛,包括海量选民签名、保证金缴纳以及参加电视辩论必需的5%民调支持率要求等。
其次是历史和意识形态视角,即美国民众自立国伊始就被分为截然不同的农业利益与金融—商业利益两大群体,在政治上表现为杰斐逊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与汉密尔顿代表的联邦党之间的政治博弈,进而形成了此后两党制的惯例,以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意识形态。
再次是文化归因,即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背景的选民都在寻求各自在美国社会中的定位,而非脱离在外,这就使得美国政党的阶级属性、选民忠诚度与政治细分度等不如一些采用多党制的欧洲国家显著,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于是成为文化意义上代表多元民众利益诉求的更具包容性的党派。
最后是选民心理,即第三党缺乏深厚的基层政治根基,多数选民担心支持第三党等同于浪费选票。
基于以上,第三党很难在美国政治中崛起为能与两大党相匹敌或至少能撬动一些议程的政治力量,其谋求执政的雄心往往也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从历史上看,第三党的兴起与衰落取决于是否拥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而其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成为“搅局者”,以对两大政党的力量对比格局产生影响来改变美国政治的结构与走向。例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9年卸任后与继任总统产生一系列分歧,随即脱离共和党组建国家进步党,该党在1912年大选中获得412万张普选票和88张选举人票,对共和党选票造成较大分流。最终,民主党人威尔逊坐收渔利当选总统,打破了共和党自美国内战后形成的一党独大格局,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第三党取得的最佳战绩。类似例子还有乔治·华莱士组建的美国独立党,该党在1968年大选中获得1300多万张普选票和46张选举人票。
“对等极化”的形成和“特朗普革命”的发生
两党制政治模式的形成虽有违美国制宪者的制度设计初衷,但其有效运转却恰恰符合并深刻反映出制宪者的根本立场,即精英主导下的共和体制。它指的是一种由民众通过选举产生代表来治理国家的间接民主,也即代议制民主。在此基础上,两党制的形成赋予这一精英共和体制以韧性,通过两党竞争和轮流执政来转移、弱化甚至消解经济社会中的各类矛盾,使美国的国家发展始终服务于精英群体的利益。
实践中,以精英共和为前提的两党制政治模式形成了由两大政党及其相应意识形态构建的传统二元分化政治结构:民主党及其代表的自由主义与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保守主义此消彼长,推动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周期性演化。按照两党力量对比(对等/非对等)与意识形态差异(极化/合作)两个维度的划分,这种二元分化结构可进一步细分为“对等极化”“非对等极化”“对等合作”与“非对等合作”四种具体形态。从美国内战后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政党政治形态为共和党及其保守主义占主导的“非对等极化”,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为民主党及其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对等合作”,20世纪70年代到奥巴马政府时期演变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对等极化”——双方在力量对比方面势均力敌,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尖锐对立。这一结果造成了政治学学者福山所论及的“否决政治”大行其道、“国家能力”日益严重缺失以及美国政治的“制度衰败”,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政治精英已经丧失了解决国家深层问题和挑战的能力,失望和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失望和不满的持续累积推动美国政治藉2016年大选爆发出一场轰轰烈烈的“特朗普革命”,矛头所指就是其发动者反复声称的“建制派”和“深层国家”——失能的精英共和体制,因而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与此同时,这场革命极大冲击了两党制政治模式。一方面,特朗普既非传统政客,亦非典型共和党人,而是在借共和党之“壳”推进其民粹主义议程,进而把共和党改造得面目全非。从某种程度上讲,特朗普本身就可被理解为一个“另类第三党”。另一方面,在特朗普及其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美国的两党政治结构日益碎片化和部落化了,不仅共和党内部出现分裂,民主党内部也发生了建制派与进步派等不同群体的争吵。
可以说,美国政治正经历从传统二元分化到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双重二元分化,即在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左右”之争以外,出现了建制主义对民粹主义的“上下”之争,从而使政治共识的形成和稳定执政联盟的构建变得更加困难,所形成的复杂混战状态和在国会中屡屡出现的按党派立场投票僵局无疑赋予第三党发挥更大作用的想象空间。
美国政党政治变局下的“美国党”
马斯克宣布成立“美国党”后,以舆论造势为主,尚未采取更多具体组党措施。毋庸置疑,这个新党在实践中难逃美国政治史上第三党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制约,短期内不可能与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但在美国政党政治进入前所未有的双重二元分化结构背景下,或许仍能发挥一些不寻常的作用。
马斯克抓住了选民对两党不满情绪处于历史高位的时机,利用其在社交平台的超高人气进行了初步的政治动员。盖洛普的民调显示,2024年自称属于“独立派”的美国人占43%,超过自称共和党(28%)和民主党(28%)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高达56%的美国民众渴望第三党打破两党垄断,其中,同时厌恶两党的“双重黑粉”选民占比达12%~17%,他们在摇摆州往往可以左右选举结果。这群选民年轻、都市化,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却对传统政治颇为冷漠。马斯克借助月活跃用户超过3亿的X平台精准触达,试图将网络怨气转化为选票。这些数据与马斯克宣称的“代表两党夹缝中的80%中间选民”说法形成呼应。
马斯克的目标是在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赢得少量席位,形成所谓“关键少数”。考虑到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两院尤其是众议院几乎平分秋色,“美国党”若能通过分流少量议席使得两大党所占议席均无法过半,其就能发挥打破僵局的关键作用。一旦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党”就能成为国会两大政党争相争取的对象,从而得以在各种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植入自己的理念、原则和偏好。
两大政党内部“异端”近年来纷纷崛起,比如共和党内的右翼民粹派和民主党内的左翼进步派,这就意味着两党内部都出现了对既有体制和结构不满并试图对本党进行重塑的力量,马斯克在两党之外“另起炉灶”也就具备了更强的政治合法性和逻辑理性。在实践中,美国两大政党之间及其各自内部多个派系彼此混战的局面,为第三党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提供了更多空间。当然,政治变局也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党”究竟能走多远,将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