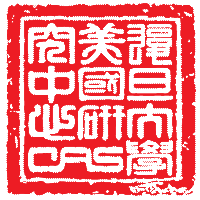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
〔提 要〕特朗普政府全面开展对华竞争,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对华施压。上述政策造成两国关系氛围恶化,战略互信受损,结构性矛盾突出,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向竞争主导型模式,双边关系缩水,在多边机制中的分歧和摩擦加剧。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依然形势严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从长远看来,中美关系走向存在多种可能,其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另一方面更取决于中国的应对。塑造推进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竞争、有效管控风险、防范重大冲突的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
〔作者简介〕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特朗普政府以战略竞争为指导思想,全面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中美两国是否会脱钩?“新冷战”是否会爆发?中美关系是否正在(或已经)跌入“修昔底德陷阱”?通过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影响,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并展望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长远走向。
一、全面开展对华竞争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宣称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性。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其对华基调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致,[1]战略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Matthew Pottinger)直言不讳地宣称,特朗普政府已将竞争的概念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最前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顶部。[2]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接触”加“防范(或制衡)”,中美关系也一直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尽管奥巴马执政时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但是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对华竞争始终聚焦个别方面和部分领域,而特朗普政府是第一次使对华竞争全方位展开:政治上,既要阻止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又要提防中国对美国社会的“渗透”;经济上,既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又要阻止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还要改变中国的产业政策;安全上,既要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又要抑制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拓展。[3]全面竞争态势反映了美国对华认知和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为全面开展对华竞争,特朗普政府设计和实施了一系列各有侧重而又相互呼应的政策手段,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脱钩、限制和施压。
第一是脱钩。脱钩的重点之一是在高科技领域,通过阻止美国的高新技术流向中国,延缓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使中国难以快速实现产业升级或在高技术领域赶超美国。为推动中美在高科技领域脱钩,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出口控制,反对所谓强制外企转让技术的相关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限制中美技术合作与交流等。2018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要求加强对出口管制清单之外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管控。同年11月,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在《联邦纪事》上发布关于特定新兴技术管制评估的规则草案,列出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定位、导航和定时技术、微处理器技术、高级计算技术等在内的14类技术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与中方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存在着惊人的一致,其矛头所指不言而喻。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也把所谓的中国强制外企向中方合作伙伴转移技术作为施压重点。2018年8月,经特朗普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正式生效。该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审批权限,特别关注外国人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保存或搜集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的美国公司的交易,并将关键技术从“对美国国家安全必不可少或重要的科学技术”扩展至包含“新兴基础技术”。脱钩的另一个重点是在国防工业领域。为减少美国国防工业对华依赖所带来的风险,打造一个在战争环境下能够安全运作的后勤保障体系,美国正在推动中美在国防产业链上部分脱钩。2018年10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评估和加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的弹性》报告称,美国国防工业有超过280项产品的供应链严重依赖外国,特别是对中国稀土和零部件的需求很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战略性和关键作用的材料和技术的供应方面,中国已经构成了重大且不断增长的风险。有鉴于此,美国正积极寻找中国进口材料的替代来源,以及使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出中国。
第二是限制。在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正在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活动施加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的限制。美国实施这些限制措施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所谓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进行政治渗透或从事间谍活动所带来的风险。近年来,美国反华势力不断炒作所谓的中国以教育、科技、人员交流与往来为手段,对美国社会开展政治渗透或影响,美国情报机构则不断渲染中国在美间谍活动的危害。“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一份题为《锐实力:上升的威权主义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操纵或歪曲信息来影响目标受众”,甚至通过发动颠覆、渗透,以达到在他国压制言论自由、扩张势力乃至控制意识形态等目的,影响他国的认知和决策,从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4]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声称,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无处不在,形式多样,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更大。[5]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则指责中国“在努力渗透入美籍华人群体、中国在美留学生、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这些行为提升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威胁着美国的核心价值,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进程。[6]二是强调美国机构和个人在华所受到的待遇与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所受待遇不对等,因此美国应该“以牙还牙”,对中国施加对等限制。为此美国出台了众多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例如《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国防部资助那些设有孔子学院的高校的中文项目。在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宣布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项目。2018年9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美分支机构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这将使两个机构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受到更多限制。美国还收紧了对中国学者和学生发放赴美签证,包括更多更严格的背景审查、更高的拒签率,取消已向一些学者发放的十年有效签证,等等。
第三是施压。美国在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通过单边和多边手段,对中国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旨在对中国进行“惩罚”,迫使中国改变政策。经济上,美国先后宣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在此之前美国还对来自中国等国的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中国被迫反击,宣布对85%的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如此规模的贸易摩擦在中美关系史和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摩擦具有多重目的,既想打开中国市场,解决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是要迫使中国调整相关的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美国还在与加拿大、墨西哥谈判签署的《美墨加三国协议》中加入“毒丸条款”,规定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6个月的通知后即可终止此协议,并以双边协议来取代。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曾在2017年10月发布《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将中国确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协议中加入“毒丸条款”无疑是要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做出重大改变。美国还竭力打压中国信息产业的两大龙头企业中兴和华为,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挤压华为的潜在市场,防止中国在5G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在安全领域,美国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都加大了对华施压的力度。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于2018年3月签署《台湾旅行法》,为提升美台关系大开方便之门。特朗普政府还对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马三国与台湾断绝“邦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建交不满,召回驻三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美台军事与安全合作也有显著提升,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次数大幅增加。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加大了空中战略力量在南海的投射力度,[7]并拉拢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盟国在南海展示军事存在。美国军方还以中国在南海的“持续军事化行为”为借口,取消了对中国参加2018“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的邀请。更有甚者,美国竟以中俄军事合作为由,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在外交领域,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提出“印太经济构想”,与日本和澳大利亚联手成立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加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全政府”行为。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调,“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最高优先,为此需要将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及军事等国家权力在内的要素整合起来,以保护和巩固国家安全”。[8]纵观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践,经济、外交、安全、执法等部门紧密配合,协调行动,这对一向被认为内部协调能力差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实属罕见。二是动作力度大,行为粗暴。无论是采取大规模的加征关税措施,或是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亦或是取消对中国军方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美国出手凶狠,不计后果。三是以经济竞争为主,外交与安全竞争的分量在上升。特朗普政府视经济安全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对华竞争从贸易摩擦入手,重点则是高科技领域。随着鹰派人物蓬佩奥和博尔顿先后出任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特朗普政府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华施压增大,安全与经济手段相互配合,呈现出“两手硬”的特征。四是注重运用多边手段。特朗普政府外交上偏好单边主义,但在对华问题上却高度重视发挥盟友和伙伴的作用,如在经贸问题上利用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等国,在南海问题上调动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在牵制“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利用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自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有些可能是短期的,有些则是长期的;有些是个别问题上的,有些则是结构性的。
第一,中美关系氛围恶化。随着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将中国锁定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及其团队对中国进行大肆污蔑和攻击,尤以2018年10月副总统彭斯讲话为甚,严重毒化了美国对华舆论环境,一时间美国出现了反华大合唱,政府和国会联手抨击中国,共和、民主两党一致对华强硬,媒体、智库跟风炒作,美国政治精英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的如此集体非理性和歇斯底里的情况,在后冷战时代还是第一次。[9]
第二,中美战略互信严重受损。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到彭斯对中国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从发动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到对华采取各种限制、打压措施,美国的种种言行不能不使中国严重怀疑特朗普政府(至少是其中的某些鹰派人物)企图对华发动“新冷战”,以实现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做法也使美国的信用度大打折扣。与此同时,美国朝野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大肆歪曲、抹黑,甚至用阴谋论阐释中国的战略意图,也加剧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疑虑、焦虑和恐惧心理。
第三,中美结构性矛盾突出。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渲染中美结构性矛盾,包括力量对比的矛盾——美国要保持霸主地位,防止被中国赶上和超越;利益分配的矛盾——美国认为中国从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对美国不公平,占了美国的便宜;制度的矛盾——中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中美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国发现不仅无法在这方面改变中国,而且中国似乎还有意对外推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国际秩序上的矛盾——美国自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缔造者,这个秩序对美国有利,而中国则意图颠覆、削弱当下的国际秩序,打造一个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秩序等。虽然中美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和分歧,但特朗普政府出于强化对华竞争的需要,故意夸大、歪曲事实,抹黑中国,使得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
第四,两国关系模式转型。在后冷战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关系始终是协调、合作与摩擦、竞争并存,协调、合作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而对摩擦、竞争的处理也不断考验着双方对两国关系的管理能力。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为竞争导向,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在缩小、合作的动力在下降,而竞争领域扩大、竞争力度大幅上升。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换到竞争主导型模式,竞争正在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第五,中美协调机制停摆。特朗普执政后双方同意建立的四大对话机制在2018年仅举行了外交与安全对话,而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三个机制停摆,许多其他双边磋商机制也无法运作。需要强调的是,中美对话机制不能正常运转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尤为深远。在21世纪初,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多,双方建立了众多的对话与磋商机制,“这些机制在沟通彼此关切、推动解决两国间的分歧、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0]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两国关系的机制化水平以及机制的有效运作是支撑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一些鹰派人士希望减少而非保持中美之间的机制化、常态化互动,鼓吹与中国打交道时对抗和施压比对话更有效,这不仅导致中美互动的“去机制化”,还有可能使摩擦和对抗取代对话与磋商而成为中美互动的主导范式。
第六,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大幅减少。由于美国加大政策限制,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下跌83%,降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11]货物贸易方面,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同比增长8.5%。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1.3%;进口增长0.7%。[12]虽然中国对美出口额有较大增长,但这主要是美国进口商为预防中美贸易摩擦在2019年进一步升级而采取的提前补仓措施,这意味着2019年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不能结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将会有显著的回落。在人文交流方面,美国在“踩刹车”甚至“开倒车”,一些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被终止,一些美国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正在有选择地对中国学生学者关上大门。长期以来,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蓬勃发展的经贸联系使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之间有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关系,给各自国家带来了巨大收益;人文交流加强了两国民众之间的联系和理解,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中美建交以来,尽管两国政治关系起起伏伏,但双方都致力于鼓励、支持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中美之间的经贸和人文纽带不断扩展,蔚为大观。当下特朗普政府限制中美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发展的政策正在严重削弱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无异于要扭转两国关系过去四十年发展所形成的积极势头。
第七,由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中美在多边机制中的分歧和摩擦加剧。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和美国贸易政策的审议过程中,中美代表针锋相对,美国提出的“重新审查中国WTO成员身份”的提案被70个成员一致否决。在WTO改革议题上,中美的角力也如影随形。在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上,中美就贸易、投资等问题激烈交锋,美国欲将其关于WTO改革的立场写进领导人宣言,中国则坚决反对,由于分歧严重,峰会未能发表宣言,这在APEC历史上尚属首次。此外,中美两国也在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内进行博弈,美国竭力拉拢其他成员对华施压,中国则坚定地抵制和反击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行为。
三、中美关系走向
在经历了中美关系激烈震荡之后,国际社会关心的两大问题是,短期内中美关系是持续震荡还是会有所缓和?长远而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否已为美国对华战略和两国关系的走向奠定了基调?
短期来看,中美关系的走向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由于民主党在美国新一届国会众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其对特朗普的牵制增大,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压力上升。经济上,2018年10月开始的美国股市大幅波动以及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意味着特朗普拼经济的努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面对愈发不利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特朗普需要与中国达成对美有利的贸易协议,才能稳定市场信心,以此作为政绩牌抵挡民主党的压力。二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各派在对华问题上影响力的变化。当前特朗普执政团队在对华问题上分成四派:以特朗普本人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主要关注美国经济利益,尤其是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经济现实主义者,主要担忧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尤其希望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新技术;以财政部长姆努钦为代表的经济自由派,关心的是中国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开放;以副总统彭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鹰派,试图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并遏制中国。[13]各派之间既竞争又合作,而特朗普一方面缺乏政策制定的全面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利用各派相互牵制,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决定取舍。目前看,前三派之间逐渐形成了共识,即通过谈判迫使中国在解决贸易不平衡、保护知识产权和停止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开放服务业市场等方面做出让步,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三是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由于中国对美国发起贸易摩擦采取了坚决斗争的立场,美国“易胜”“速胜”的幻想破灭。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两国以积极务实的态度重开谈判,有希望在2019年上半年结束这轮贸易摩擦。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即使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定,中美经贸摩擦仍将起起伏伏,美国不会放弃在科技领域的对华限制和打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贸易摩擦休兵,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安全鹰派有可能在外交与安全问题上加大对华压力,如为了支持台独势力继续执政而加大对台支持力度,或为在南海问题上“推回”中国的战略布局而升级对华挑衅,在涉疆、涉藏、涉港问题上也会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而特朗普政府剑走偏锋、出手凶狠的行事风格也增添了双边关系的风险。因此在中美关系的重要转型期,摩擦、颠簸和冲突越来越成为常态,有效的风险和危机管控对双方都是紧迫的需求。
长远而言,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仍未完全定型。就美国对华战略而言,强化对华竞争、加大对华压力已是基本共识,但当下美国朝野对华强烈的情绪化反应和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和风格所带来的政策影响都未必能够持久。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强大、有所作为的中国,如何设计一项更加有效的对华战略这一问题,美国内部尚在探索和辩论之中。[14]美国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如何确定对华关系的终极目标,应在对华关系中采取哪些手段,准备付出哪些代价,这些尚未形成共识。[15]美国各派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不仅是一个认知和偏好的问题,更涉及不同利益的博弈。最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的走向,而展望未来,美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16]
在后冷战时代,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谋求经济利益是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在中美之间始终存在诸多政治与安全分歧的背景下,经济联系成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和粘合剂。鉴于经济因素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经贸关系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从美国国内对华经济思维看,至少存在三种形式的对华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对整个双边关系意味着不同的后果。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此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会起伏不定、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也难以建立互信。另一种是经济现实主义,它关心的是经济交往不会增强对手至关重要的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对手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己方的实力差距,因此在经贸关系中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这样的对华经贸政策会导致双边经贸关系缩水,其外溢效应也会使得政治与安全关系充满摩擦,冲突的风险会上升。还有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它从全球化视角看待对外经济交往,主张按照多边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谋求共赢。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会在互补与竞争中继续发展,政治与安全关系也会体现出合作与竞争交织的特点。
此外,在美国对华战略与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其主要体现在力量、利益和认知三个维度。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是美国对华战略要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美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总体而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将继续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必须适应这样的新现实。第二,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对华关系的状态,中美势必要重构两国利益关系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重构已经开启。在此过程中,利益的竞争固然会加剧,但利益的协调和交换也至关重要。尽管美国越来越注重短期收益和相对收益,这增加了中美利益博弈的力度和难度,但中国注重长远和大局的思维方式则为双方利益协调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第三,当前美国正在形成更加负面的对华和对双边关系的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可以通过有效的行动和沟通让美国认识到,双方在经贸以及地区与国际事务上有着合作的现实需求和巨大潜力,中国不只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也是美国的重要伙伴。面对“两国在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的趋势”,中国要强调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淡化双方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管控意识形态分歧。[17]在美国越来越以零和思维、竞争思维看待双边关系时,中国应强调确立“稳定、协调、合作”的双边关系基调的重要性,[18]继续倡导中美应谋求建立与21世纪时代潮流相吻合的新型大国关系。
四、结语
在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变化和战略与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序幕已经拉开,摩擦的激烈程度和广泛程度在后冷战时代前所未见。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战略、政策及战术手段上的调整,使得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形势严峻。但长远看来,我们不必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两国关系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同时更取决于中国的影响与应对。塑造一个推进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竞争、有效管控风险、防范重大冲突的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方向。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9,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上网时间:2019年1月20日)
[2] Jeremy Goldkorn, “Trump Official Matt Pottinger Quotes Confucius, in Chinese, to Make Point about Language and Truth,” Supchina, October 1, 2018, https://supchina.com/2018/10/01/matt-pottinger-quotes-confucius-in-chinese/.(上网时间:2019年1月20日)
[3] 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88页。
[4] 胡泽曦:“‘中国威胁论’为何成华盛顿‘心魔’”,《环球时报》2018年3月1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3/11631883.html。(上网时间:2019年1月25日)
[5] 李勇、任重、倪浩:“‘抓中国间谍’竟成FBI头号任务”,《环球时报》2018年9月15日,第8版。
[6] Larry Diamond and Orville Schell eds., China’s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8,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00_diamond-schell-chinas-influence-and-american-interests.pdf.(上网时间:2019年1月25日)
[7] 据统计,2017年美军一共在南海开展4次“航行自由行动”,派B-1B远程轰炸机飞行2次;2018年开展“航行自由行动”5次,航母在南海地区游弋2次,B-52轰炸机飞越5次。
[8] The 115th Congress, H.R. 5515, 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515/text.(上网时间:2019年1月26日)
[9]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指出,“有一个外交领域正在迅速达成共识,这个领域把特朗普一派、民主党人、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几乎所有外交政策评论人士团结在一起,这就是中国”。见Daniel W. Drezner, “The China Gap,”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1/31/china-gap/?noredirect=on&utm_term=.3825ce39e467;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华盛顿针对“中国威胁”掀起了一场“政治海啸”。Charissa Yong, “US Should Engage in Smart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Straits Times, February 14,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us-should-engage-in-smart-competition-with-china。(上网时间:2019年3月13日)
[10] 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11] 据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2016年达到峰值,为456.3亿美元,2017年下降到290亿美元,而2018年则大幅缩水至48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83%。“西媒:中国去年对美投资骤降,对西加投资大增”,参考消息网,2019年1月5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90115/2368345.shtml。(上网时间:2019年2月14日)
[12] “新闻办就2018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政府网,2019年1月1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4/content_5357666.htm#3。(上网时间:2019年2月14日)
[13] Ben Smith and Peter Harris, “Trump Needs To Make Up His Mind on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26,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needs-make-his-mind-china-39842.(上网时间:2019年3月12日)
[14]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February 2019; Andrew S. Ericson,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An American Concept for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30,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mpetitive-coexistence-american-concept-managing-us-china-relations-42852.(上网时间:2019年3月12日)
[15] James Dobbins and Ali Wyne, “The U.S. Can’t ‘Out-China’ China,” The Hill, December 30, 2018,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23225-the-us-cant-out-china-china.(上网时间:2019年3月13日)
[16] 这种不确定性包括:美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前景,美国政治极化和党争的走势,美国外交内顾或外向这两种趋势哪一种会占上风等。
[17] 王缉思:“巩固共同利益,管控价值观分歧”,《世界知识》2019年第1期,第13-14页。
[18] 例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2019年“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今后的道路也已明确,就是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是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也应当成为两国各界的最大公约数和共同努力的方向。”“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外交部网站,2019年3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44074.s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