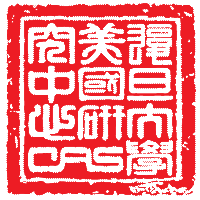我是1989年春季开始跟汪熙先生读博士的。当时他给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叫“中美关系史”,每次讲一个专题,然后布置我们看书,写读书报告。每次的读书报告他都会点评,从内容到文风都很在意。我那时喜欢给上海一家叫《书林》的杂志写文章,文风比较新潮,先生看了不以为然,认为读历史的人文风应该非常朴实,不要花里胡哨或故作高深。他特别强调史论必须得当,要分析到位,但也不能讲过头。此外,先生还与我们分享做读书卡片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他多年摸索出来的,简便而实用。这门课读下来,收获最大的就是治学方法,后来在写博士论文时都用上了。
大约是 1989 年秋,先生问我博士论文有何打算。我当时还没什么想法,于是先生建议我研究美国塔夫特政府时期的在华“金元外交”。先生告诉我,他1987年应邀到康奈尔大学讲学和研究,在康大图书馆阅读了塔夫特政府在华“金元外交”的关键人物司戴德的档案,深感塔夫特政府的在华“金元外交”是美国对华政策演变中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当时美国与日本在中国的争夺很激烈,矛盾很尖锐,这实际上是美日在华矛盾的起点。先生说,对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但中国学者研究的不多,也没有很好地利用美方的一些档案材料,如果就这个问题做篇博士论文,是有价值的。我同意了。
按照先生的要求,第一步是做研究书目,就是要把与本专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搜集完整。那时候没有电子检索手段,主要是人工检索,我花了一些时间整理了一份书目,先生看了不满意,认为还有很多遗漏,给了我一些建议。于是我再补充,做了一份更加详细的书目,这次先生认为差不多了,但强调没有把美国的一些档案材料包括进去。他希望我在写博士论文期间能够有机会去美国查阅相关档案材料,并要我做出国的准备,考托福。
那时候博士论文写作还没有开题报告一说。先生于是希望我先就这个题目写篇文章,确立博士论文的基本框架。我在1990年春夏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写成了《司戴德与美国对华金元外交》一文。先生在暑期看了以后,觉得不错,认为博士论文可以按照这个框架和思路去写。先生还建议将此文提交《复旦学报》发表,并介绍我去找学报编辑周老师。周老师收到稿件后很快安排发稿,因为文章比较长,分两期发表在《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和1991年第1期)上。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鉴于这篇文章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征得先生同意后,发表时我把先生恭列为第一作者。这是我和先生合作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此文得到先生的肯定并顺利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对博士论文的写作有了信心。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英文材料不好找,特别是美国的档案材料只能到美国去看。那时由于相关政策变化,文科博士不搞联合培养,这样我虽然托福考了高分,但也没有机会去美国做论文。凑巧的是,大约是1990年初,先生自己有机会去美国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于是他就承担起为我搜集英文材料的任务。通过邮寄或友人携带,先生先后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英文著作的复印件和档案材料,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藏于康奈尔大学的司戴德的个人档案材料(司戴德毕业于康大,去世后所有的日记、信函均捐献给康大图书馆),其中有些是翻拍的,有些是缩微胶卷。可以说,没有这些一手材料,论文的写作很难顺利完成,即使写出来了,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1991年秋,我完成了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6-1913》。次年1月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后,先生叮嘱我要对论文进行修改和扩充,以达到出版要求。1994年 1月,我赴美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利用这个机会,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塔夫特政府国务卿诺克斯的文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了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有关档案材料,对论文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先生审阅了修改后的书稿,决定将其列入他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1997年秋,我的博士论文出版,先生拨冗为本书写了“主编前言冶,在结尾处,先生写道:
“在与吴心伯博士商讨研究课题时,他不畏艰难有志于探究‘金元外交’,后来又赴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进一步挖掘梳爬有关原件和文献资料,颇有所获。吴博士是一个研究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我很高兴他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探颐索隐、钩深致远的研究,他把这一段扑朔迷离的过程理清了头绪并进行剖析。我相信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会引发中外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多的思索。”
对向来不轻易表扬学生的先生来说,以上这段话无疑是对我这段研究工作的极大肯定。领受先生教诲栽培之恩,我也有机会在自己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先生的感激之情:
“为文始末,从选题到定稿,得到汪熙先生的悉心指导。他向笔者提供的司戴德档案材料及其他大量外文资料,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先生的关怀惠我良多。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如今先生走了,但我对当年跟随先生求学经历的记忆却是那么的真切和鲜活。保持这份珍贵的记忆,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更是我在学术之路上前行的巨大动力。

全文